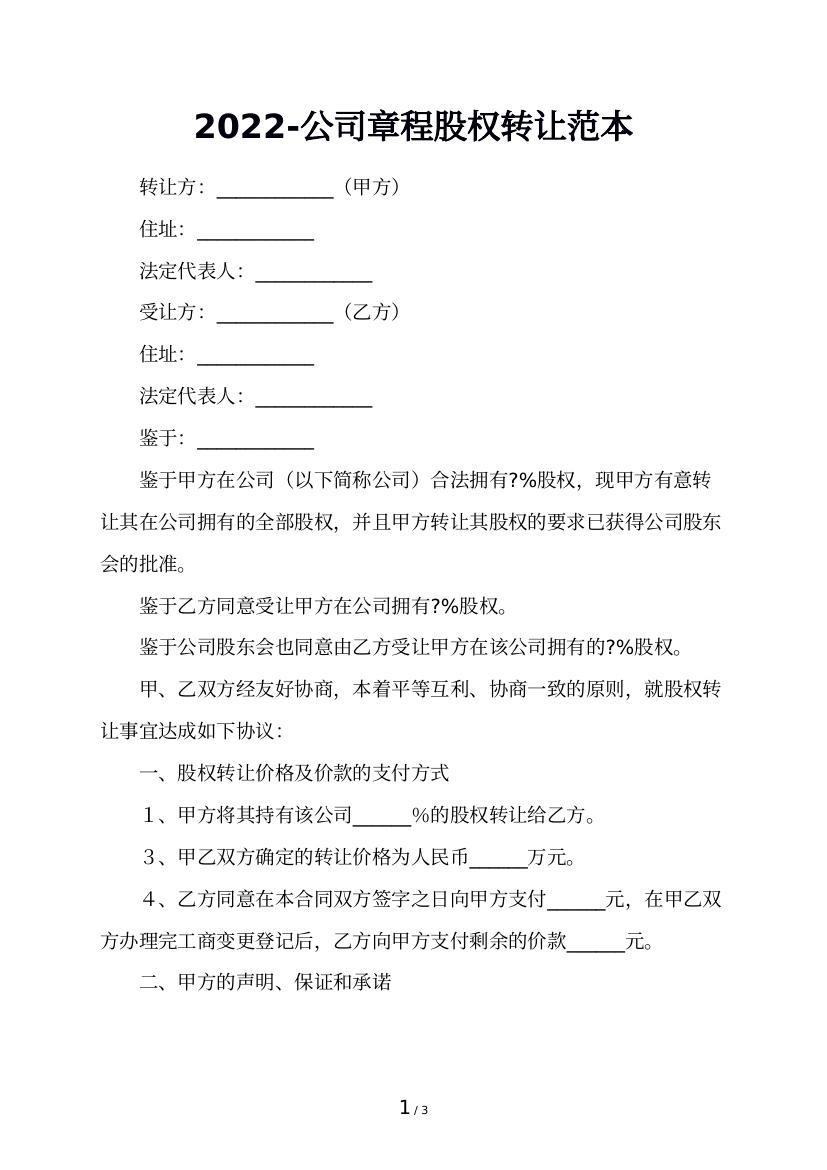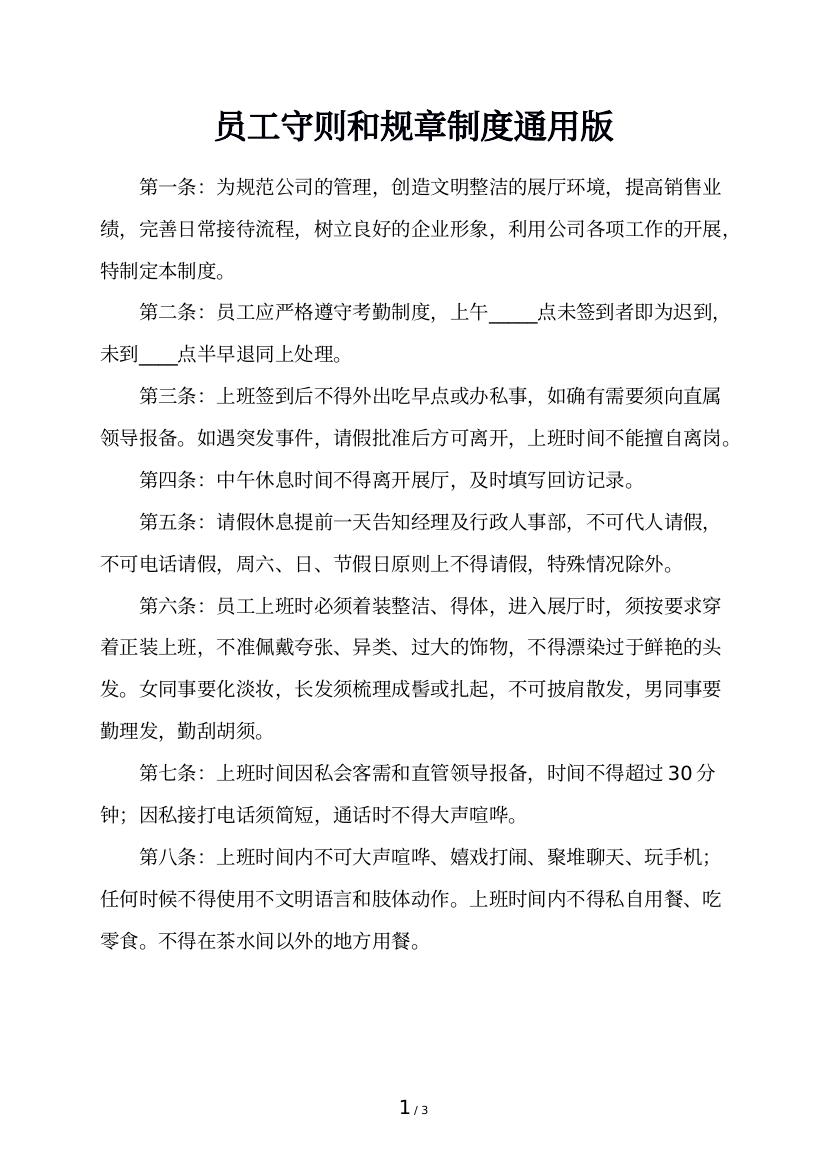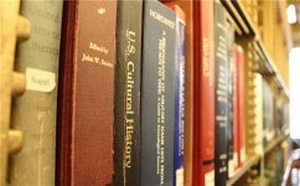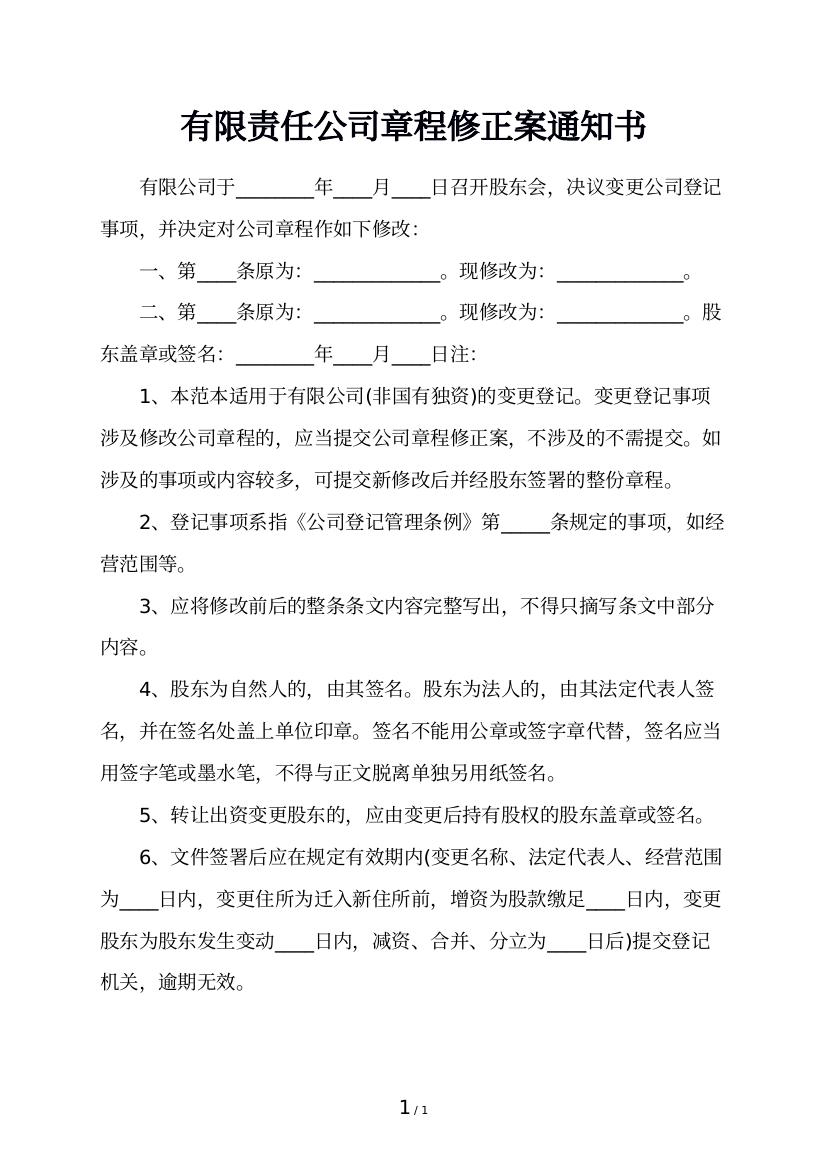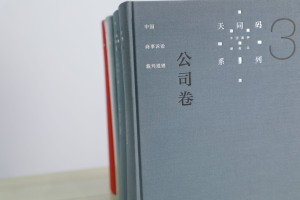在我国反收购实践中,限制董事资格条款还表现为对董事产生程序的限制。爱使股份公司章程与方正科技公司章程均存在这种董事人选产生程序的限制性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关于董事人选产生程序的限制性条款因违反股东选择管理者这一基本股东权而应认定为无效。但由于旧《公司法》对股东提案权的保障性程序规定不够明确,因而在该法框架下还不能得出明确的无效结论。爱使股份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人选须在听取股东意见基础上,由董事会审查、确定候选人名单。方正科技公司章程也规定,董事会有权对董事的资格进行审查。正是根据该规定,爱使股份与方正科技均拒绝了收购人提出的增补董事的人选。对此,旧《公司法》未就股东大会的提案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因而爱使股份公司章程与方正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并未直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57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新的提案。”依此,收购人应能向公司提出增补董事的提案。但由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效力,若公司章程未作此规定,则不能依此获得董事提案权。不过,依新《公司法》,上市公司已不能采取这种明显规避法律的措施。
新《公司法》第103条第2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依此,只要收购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即可向董事会提交增补董事的临时提案,而董事会必须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由此可见,在新《公司法》框架下,通过公司章程对董事、监事产生程序作违反该法规定的限制性规定,已明确违法,从而完全失去其反收购的效果。(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注释:[1] 参见[美]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则》,胡平等译,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 - 468页。
[2] 上市公司收购往往导致目标公司的管理人员被解职,普通员工也可能被解雇。为了解除管理人员及员工的这种后顾之忧,美国有许多公司采用金降落伞、灰色降落伞和锡降落伞的做法。金降落伞是指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由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者与公司签定合同规定:当该公司被收购且其董事及高层管理者被解职时,可一次性领到巨额的退休金(解职费) 、行使股票期权或获得额外津贴。灰色降落伞是指公司承诺,若该公司被收购,中级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工龄长短领取数周至数月的工资作为补偿。锡降落伞是指若公司普通员工在公司被收购后一段时间内被解雇,则可领取一定数额的员工遣散费。
[3] 参见[美]托马斯。李。哈森:《证券法》,张学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7页。
[4]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Pisohel, The Proper Role of a TargetManagement in Responding to a Tender Offer, in Harverd Law Review(1981) , pp. 1180 - 1182. [5] See John C. Coffee, Regulating the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A CriticalAssessment of the TenderOffer‘s Role in Govern ance, in Columbial Law Review (1984) , pp. 1183 - 1192. [6] 所谓三无概念股,是指股本结构中既无国家股,也没有法人股和外资股,全部股本构成均为可流通的社会公众A股。
[7] 参见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8] 参见冯果:《公司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 - 122页。
[9] 参见范健、王建文:《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冯果:《公司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范健、蒋大兴:《公司法》(上卷)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10] 参见林新:《企业并购与竞争规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1] 参见前引9,范健等书,第205页。
[12] 参见周友苏:《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 - 384页。
[13] 参见雷兴虎、胡桂霞:《论董事行使职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制衡机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