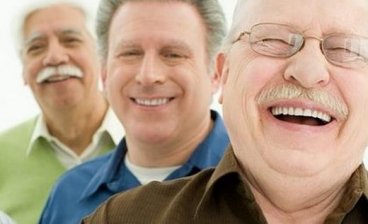本条法条构建了合同条款解释的完整规则体系,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平衡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交易公平。
一、合同解释的基础与参考因素
第一款确立 “以词句通常含义为基础” 的首要原则,文字是意思表示的直接载体,是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起点。如买卖合同中 “交货地点” 的解释,首先依据普遍理解。
在此基础上,需结合多层因素综合判断:相关条款要求结合合同整体解读,避免断章取义;合同性质和目的是解释导向,如赠与合同条款解释需符合无偿本质;习惯包括交易、行业惯例;诚信原则保障公平,格式条款解释倾向保护非提供方;缔约背景、磋商过程、履行行为等动态因素,助力贴近实质合意。
这一体系突破单一文义局限,让解释更贴合真实意思,也为法官提供裁量空间。
二、当事人共同理解的优先性
第二款明确 “当事人共同理解优先于通常含义”。合同是意思自治产物,若双方对条款有不同于通常含义的共识,且有证据证明(如磋商记录、函件等),该共识优先。
此规则需满足两条件:有证据证明共同理解存在,且为双方一致认知。如建材买卖合同中 “行业标准”,通常指国家强制标准,但若有会议纪要证明双方约定以某协会标准为准,法院应优先采纳。这可防止一方事后背离真实合意,维护意思自治。
三、特殊场景的解释规则
第三款针对两种情形设定倾向规则:
一是有利于条款有效的解释。当条款有多种解释且影响效力时,选使条款有效的解释。这体现 “尽量维持合同效力” 理念,鼓励交易,如合作协议 “利润分配比例” 有歧义,应选可确定比例的解释。
二是无偿合同中对债务人负担较轻的解释。无偿合同中,债务人无对价却承担义务,解释应减轻其负担。如无偿保管合同 “保管责任” 有歧义,应选要求保管人承担较轻责任的解释,符合公平原则。
司法实践意义
本条构建 “一般 — 特别 — 特殊” 递进体系,规范法官裁量权,减少同案不同判;引导当事人明确条款含义并留存证据;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减少合同无效情形。其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兼顾公平与效率,是维护交易秩序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