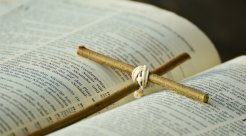本案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吗
林天文 福建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
[内容提要]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受民事法律的调整,在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协议有效,双方应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在普通商业经营的拆迁活动中,拆迁人不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虽然拆迁人是国有企业,但是在拆迁业务中并不能说是直接代表国家利益,以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要求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不妥当。
[关键词]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国家利益 国有企业 信赖利益保护
[案情]
原告李A、 李B(系被拆迁人,系同胞兄弟)
被告福建省XX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系拆迁人)
原中山西路186号店房于1943年XX伪县政府发有1607号土地所有权状,1952年XX县人民政府对该土地所有权状作了验证,该土地所有权状注明该幢店房的种类为市屋,层数为两层,式样为中西式,材料为砖瓦,面积是二分六厘七毫(约178平方米)。1985年4月9日原XX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岩中法(85)民上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原XX市中山西路186号店房前节楼房归李B(原告之父)、李D(原告之叔)和李F(原告之堂叔)所有;后节楼房归李B、李D兄弟所有。判决生效后,在法院主持下进行房产分割,将前节一分为二,西边的归李F,东边的归李B、李D。1987年10月10日,原XX市中城办事处司法办对李B和李D的房产进行了分割,约定一层前节归两人共有,中节一层归李B所有(注:其他部分与本案无关,不提),随后,李B及其继承人约定,该处房产李B的份额归李A、李B兄弟所有。1991年9月28日,原告李A、李B取得了原XX市土地局颁发的龙国用(91)字第029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998年1月,原告办理了中山西路186-2号(即中节)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龙字第20833号)
原中山西路186号底层示意图:
中山西路
|
前节 19.7㎡ 19.7㎡ 186-1 186-3 李C 李A、李 B、李D
中节 186-2(46.37㎡) 李B、李F |
|
后节 |
1992年5月20日,原告二人与蒋某签订《店房租赁合约》,将原中山西路186-3的二分之一及中节约40㎡租给蒋某经营使用。此后,该部分曾先后出租给李某、郑某等经营使用至房屋拆迁。拆迁前是曹某经营的龙岩市新罗区中城笑琼窗帘店(领有工商营业执照),在龙岩市中山路三期改造中,原告于2000年4月29日8时腾店交付给拆迁人,办理店房补偿安置的手续顺序单是20号。2000年4月29日拆迁机构制作了房屋使用性质及面积认定表,表中注明需确认情况是原告店房中节(46.37㎡)要求认定营业性用房面积,产权确认情况是认定店面面积23.45㎡(折合10米以内),2005年5月5日重新认定结果是10米以内3.157㎡,10米外为43.213㎡,折合10米以内店面面积24.76㎡。规划、土地、房管部门均盖章确认。2000年5月6日被告委托的拆迁实施单位龙岩市拆迁安置服务站制作的李忠星、李忠友户龙岩市城市房屋拆迁评估情况表,确认原告的被拆迁店房主街10米内店面面积为29.60㎡,其中包括前节9.85㎡和中节19.75㎡(中节由行政机关认定的24.76㎡减少至19.75㎡)。龙岩市拆迁安置服务站、龙岩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被拆迁人(原告)都在该评估情况表上签字,并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同日,原被告签订《店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原告被拆迁店房面积(10米以内)为29.6㎡,安置店房是中山路三期7号楼7-105-2#店,2001年12月19日拆迁人通知被拆迁人(原告)于2002年1月4日开始交付安置店房,办理回迁手续。但是当原告前往要求办理回迁手续时,被告拒绝。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原告于2003年4月2日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店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交付安置店房。案件在审理过程中,2003年3月19日龙岩市房管局等单位对原告的店房的使用性质重新认定,认定前节9.85㎡为营业性用房,中节46.37㎡为住宅。在事隔一年多之后,龙岩市房管局于2004年4月28日才将认定结论通知原告。2004年5月9日民事案件作出裁定,由于市房管局对原告的房屋使用性质重新进行了认定,可能对民事案件的处理有影响,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原告不服市房管局的重新认定,开始行政诉讼,经过一审和二审,二审法院于2005年5月30日判决撤销2004年4月28日房管局的重新认定。龙岩市房管局收到判决后又于2005年7月21日重新作出《关于原中山西路186号店房李忠星、李忠友户房屋使用性质重新认定结论的通知》,重新认定原告店房的中节为住宅。原告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审理,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岩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龙房综[2005]51号重新认定通知。随后,原来中止的(2003)龙新民初字第553号民事案件恢复审理,因龙岩市房管局的认定与本案有关联,原告不服(2006)岩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向龙岩市中级法院申诉,并于2008年1月3日向区法院申请撤诉,2008年1月10日区法院作出(2003)龙新民初字第55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经原告申诉,龙岩中院于2008年10月28日裁定进行再审,经过审理于2009年2月16日作出了(2008)岩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龙岩市房管局于2005年7月21日作出的龙房综[2005]51号《龙岩市房管局关于原中山西路186号店房李忠星、李忠友户房屋使用性质重新认定结论的通知》。行政判决生效后,原告要求被告交付中山街壹层7-105-2#安置店房,但是被告仍然以种种理由推诿,拒不交付安置店房。原告再次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履行《店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交付安置店房。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龙岩市房管局又通知原告,决定再次对原告店房进行重新认定。
被告认为,根据《龙岩市中山路改造建设第三期拆迁计划和补偿安置方案》,动迁一间店在主街安置一间,原告和李永旭、李忠辉等原中山西路186号店面业主只能在中山路主街安置一间店面。原告店房的中节不是营业性用房,拆迁前认定为营业性用房是错误的。因此,原告以欺骗手段签订的《店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损害了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属无效协议。被告不同意履行原拆迁安置协议,被告将根据行政部门的认定意见,结合《龙岩市中山路改造建设第三期拆迁计划和补偿安置方案》对原告和李忠辉、郭枫、李永偕等原中山西路186号的被拆迁户进行补偿安置。
[评析]
一、国有企业利益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利益。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先不说原告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是否使用了欺诈、胁迫的手段,首先就是否损害国家利益作一简述。
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指国家政权和行使政权的国家机构体系。例如,列宁曾把国家比做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这个机器是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官僚集团所组成的一套机构,是来自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① 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对社会实行统治的机关;国家是人口、领土、主权三者的总合体。 ② 国家的概念是抽象的,国家利益也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国家利益是指国家政权的利益,是公法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是与国家主权相联系的。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利益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利益。虽然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为国家或者是政府,但是国有企业也是民事活动中的平等主体,国有企业进行民事活动时也受民事法律的调整。《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经营的法人,进行民事活动时是平等民事主体的一员,它不具有超越其他主体的特权,在法律上没有特殊的保护。试想,如果国有企业拥有特别保护权,动辄以损害国家利益为由提出合同无效,其它主体中有谁还愿意与国有企业进行交易?最终受到损害的也是国有企业自身的利益。平等原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合法利益受法律平等保护是平等原则的题中之义。国有企业与所有的市场主体一样,适用同样的市场规则。一旦国有财产授权给特定的企业进行经营,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财产与私有财产受平等保护。国有企业最终的财产权属全民所有,但是表现出来首先是企业利益,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企业出资者也不能过分干预。例如,中国电信是国有企业,财产属全民所有,用户是与企业发生交易,而不是与国家直接发生经济交易。用户与中国电信签订的合同即使是损害了中国电信的某些利益,电信用户也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认为合同无效。
马克思认为社会本身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组合,政治国家是公权存在的基础,而市民社会是私法存在的基础。“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 ③ 在民法调整领域不能体现高高在上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应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权利中。如果将国家利益掺杂在拆迁合同关系中,那就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了,应是公权力介入的行政法律关系,不受民法调整。出现的后果是国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造成市场经济的混乱,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二、行政机关对房屋使用性质反复认定,违反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
原告的房屋是否为非住宅营业性用房,对拆迁补偿安置结果影响很大。作为被拆迁人,原告是在行政机关认定其房屋基本上为营业性用房,店面折合主街10米以内29.6㎡的情况下才与拆迁人签订店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相信行政机关认定的非住宅营业性用房面积不会改变,拆迁人也会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产生一种信赖利益。信赖利益是应受法律保护的。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涵义是,行政相对人因为信赖既存的行政法秩序而安排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则不能因为后来的行政行为的变动而使其遭受不能预见的损害。该原则要求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④ 本案涉及的房屋使用性质认定机关所作认定随意变更、反复无常,使相对人陷入迷惘,使其权利受损害。在现代法治思想下,不能机械地理解“依法行政”的概念,即使具体行政行为有错误,也不得随意撤销与变更,撤销与变更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如,《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是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本案行政机关在房屋拆除后两次作出的重新认定,经过行政诉讼,最终两次重新认定均被法院撤销,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行政机关再次通知原告准备对房屋使用性质作出重新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不管结果如何,对本案的民事权利义务不会产生影响,拆迁安置协议的人应严格履行安置协议,拆迁人应按约定交付安置店房。
笔者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店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协议双方应全面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参考文献:
①《法理学》,张文显主编,法律出版社。
②《政治学》,作者阎铁力、沈火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③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④ 吕艳辉:“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论析”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