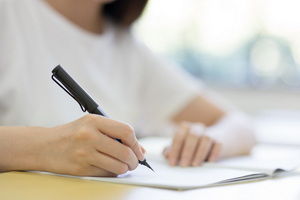陈某在上海某地做保姆期间盗窃雇主财物,被上海某地公安机关取保期间,在取保候审期间又到浙江某省做保姆,再次盗窃雇主财物,又被浙江某地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在上海某地法院判决宣告缓刑后,浙江某地法院的盗窃案也宣告缓刑。造成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适用强制措施及判决错误,原因是两地司法机关对异地犯案都不知情,陈某认为司法机关输入身份证号码就知情。那么,是陈某的隐瞒不告,还是陈某的认知错误,这个案件最终会怎么处理呢?我为了了解案情,正在前往会见和阅卷。
会见阅卷 熟悉案情
2024年4月份,我接受当事人陈某家属的委托,开展了一起再审案件的辩护工作。我接受委托时,陈某已被羁押在看守所,为了了解陈某的案情和诉求,决定先去会见陈某。在看守所会见室里,我表明了身份后,铁栅栏对面的陈某留下了眼泪。在陈某平复情绪后,向我诉说:
她原来做过培训,还做过其他一些生意,结果亏进去好几百万。2023年5月初,她因生活的压力去了上海某地做居家保姆,但是催债不断,两个小孩、年迈残疾老人需要费用,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于是拿了雇主卧室床头柜内的手机,分三次扫码转账了15800元。
她因这个事情,在2023 年 5 月 中旬,被上海某地公安局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经上海某中介介绍来到浙江某地做保姆,在2023 年 7 月中旬,她又拿了雇主存放在酒窖里的酒卖了 12700 元,该事被告发后,浙江某地公安局于2023 年 7 月 21 日也对她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
到了2023 年 9 月 15 日,上海某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后来由她经常居住地执行缓刑。2023年12月12日,浙江某法院判决她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浙江某法院将缓刑送交她的户籍地执行。
在送交执行的过程中,她发现这样不对,就向浙江某法院承办人员告知了这个事情,也向经常居住地的执行缓刑的部门反应了这个事情,执行缓刑的部门还来过浙江某法院调查。之后,浙江某法院说这样判有问题,提出要再审,她也就被羁押进来了。
说完了之后,我接着问,你为什么不把两地犯案的情况向两地司法机关报告。她回复我:她认为办案机关是联网的,把她的身份证号码输入进去,司法机关就能知道她的犯案情况,认为不需要主动报告的。
会见后,申请了阅卷,我针对会见了解到情况,与案件一一作了核实,基本情况与陈某会见陈述的基本一致。
苦思冥想 寻找辩点
我了解案情后,我总感觉,在这个案件中,有两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再审案件的结果,第一个是前罪取保期间又犯罪,前罪执行缓行期间又判缓刑,司法程序该怎么走,因为不同的程序会影响到量刑。第二个是她有前科隐瞒不告,还是她认知错误,这个也会影响量刑,还会影响到裁定的执行方式,也就是实刑还是缓刑。
自从接触这个案件后,这两个问题总是浮现在我得大脑中,从事实层面,转从逻辑层面,又转到法律层面,并不断得反转,思考、推敲、凝练,希望能够找到案件辩点,孕育出一个既能稳妥落地,又能切实维护陈某权益的完美方案。
律师考虑问题是有期限,且这个期限由审判机关决定。也就是说,律师的观点应当在庭审前应当基本完成,庭审时或庭审后作适当调整。陈某的案件,在庭审前也形成了一个辩护的初步方案,找出了如下的庭审辩点。
对于第一个问题,前罪取保期间又犯罪,劈开两地司法发机关后面进行的司法程序,应当由两地侦查机关确定管辖后,并案侦查、起诉及审判。但在本案再审前两地司法机关各自走完刑事诉讼程序,这个案件是否在再审查明事实后,是否依旧由公诉机关撤回起诉,退回公安呢?还是在再审查明事实后,对浙江某检察院指控的盗窃罪案进行判决,然后与上海某法院已判刑罚进行数罪并罚呢?我认为由两地原公诉机关撤回起诉,退回侦查机关,然后在确定管辖后并案侦查、起诉和审判,这些重来的繁琐诉讼程序会给陈某带来的讼累。同时,并案审理因盗窃数额按累计量刑,后罪量刑后按数罪并罚决定刑罚的执行刑期,这两者相比之下,按数罪并罚处理对陈某会更有利。
对于第二个问题,陈某认为办案机关是联网的,把她的身份证号码输入进去,司法机关就能知道她的犯案情况,认为不需要主动报告的,她说的是否可信?即便是这样,是否可以隐瞒不告,还是认定认知错误,再审后是否还能宣告缓刑?我考虑到了法律的规定上,引起再审的原因,陈某家庭情况等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法院宣告缓刑的理由也存在一定的辩护价值。
是骡是马 法庭上见
自己生的娃,再丑也是咱自己,可以怎么看怎么喜欢。但是,律师形成的辩护意见,是骡子是马需要拉出来溜溜,需要在法庭上见分晓。
再审庭审开始了,我带着酝酿好的辩护方案,依法参加庭审活动,在法庭调查阶段,我对案件关键问题向陈某进行了发问和核实,在法庭辩论阶段着重对以上两个问题提出辩护人的解决方案。
对于并案处理还是数罪并罚?我庭审提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建议再审案判处的刑罚,与上海某法院已判刑罚,按法律规定的数罪并罚处理。
我陈述的理由是,从法律层面上讲,我国《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进行数罪并罚。但是,本案的情况与该条文规定不符,在浙江某法院宣告缓刑之前,陈某的前罪已由上海某法院作出判决,不是条文中的 “没有判决”,显然本案不符合这个条文的规定。对于这种情况,虽然不符合该条文规定,但我认为,可以参照该条文规定的立法精神予以处理。从司法实践层面上讲,在审理前罪的过程中,异地法院已经对后罪作出判决,因两案未能合并审理,将前罪判处刑罚,与异地法院的后罪进行数罪并罚的案例,这种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值得借鉴。
对于未报告前科是否隐瞒还是认知问题,能否宣告缓刑 ?我认为还是宣告缓刑比较妥当。
我陈述的理由是,从引起再审的原因上看,因两地法院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作出缓刑判决,这与陈某不及时反映情况有一定关系,但这不完全是陈某故意为之,也存在了陈某一定的认知错误。同时,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是有明确禁止规定的,而对于数罪并罚,法律上并没有限制宣告缓刑的适用,既然原两地法院都考虑宣告缓刑,数罪并罚后依然可以宣告缓刑。从家庭情况来看,陈某尚需抚养两个小孩,还需照料残疾年迈的老人。
谜底揭开 法官说法
案件审理完毕后,陈某前罪取保期间又犯罪,前罪执行缓行期间又判缓刑,原因是两地司法机关对异地犯案都不知情,陈某认为司法机关输入身份证号码就知情。那么,是陈某的隐瞒不告,还是陈某的认知错误,是按数罪并罚还是并案审理,能否判宣告缓刑呢?很快就见分晓了。
2024年5月23日,浙江某法院经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某法院刑事判决;二、撤销上海某法院刑事判决对陈某的缓刑宣告部分;三、原审陈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与上海某法院刑事判决前罪没有执行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实行并罚,合并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
从以上再审判决中可以看出,我提出建议本案判处的刑罚与上海某法院已判刑罚按法律规定的数罪并罚处理的观点得到浙江某法院认可,对陈某数罪并罚后建议继续宣告缓刑的观点,因法院认为陈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犯罪,并隐瞒其他犯罪事实,主观恶性较大未予以采纳。
判决后,我师对陈某进行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我询问陈某对我的服务是否满意时,陈某说:“很满意,很负责任,虽然法院没有全部支持辩护观点,但你的辛苦和努力我看得到,谢谢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