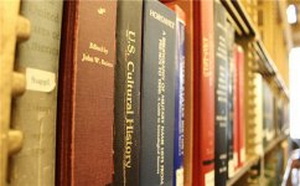关于盗窃罪有关问题的探析― 兼议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部分条款内容摘要:盗窃罪作为一种高发性犯罪,历来是国家打击的重点,但最高院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未遂的处理、对多次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的认定以及对盗窃累犯的处理存在诸多缺陷与矛盾,本文试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对该解释有关条款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关键词:盗窃罪 司法解释 问题 探析 盗窃罪是一种常见罪、多发罪,历来是刑法打击的重点。近年来,盗窃案件居高不下,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各类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修订后的刑法对盗窃罪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解决了司法实践中不少难题,对有效的打击盗窃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在审判实践中具体问题比较复杂,刑法修订后施行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便又作出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刑法中不详尽的部分又作了规定,为指导审判实践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该《解释》部分条款存在着一些制定缺陷,导致一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论,难以把握,并造成执法的不统一。现结合该解释的部分条款就盗窃案件中的有关问题发表一些个人浅见。 一、关于盗窃未遂的定罪处罚问题 《解释》第1条第(2)项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按照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盗窃未遂的行为人无法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如某行为人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刑满释放后2年内又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在盗窃过程中因被事主当场抓获而未遂,根据上述规定,只有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而未遂的才定罪处罚,显然以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的并且还是累犯的该行为人的未遂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对该条款的适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目标的盗窃未遂行为是否的确不构成犯罪?易言之,这种行为是否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是否就不应该追究法律责任?此规定到底有无道理或法律依据? 对于未遂犯的处理,我国《刑法》第23条明确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此规定,对未遂形态的犯罪作出了界定并规定了处罚原则,从字面意义上看,本规定没有排斥盗窃犯罪的未遂,因此,对已经着手实行盗窃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应认定是盗窃罪未遂,该条款就是盗窃罪未遂行为应当受到刑事追究的法律依据。从盗窃未遂案件的基本特征来看:在社会危害性方面,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目标实施盗窃,虽然未遂,但也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危害性较大;在刑事违法性方面,这种行为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虽然行为未遂,但其刑事违法性依然存在;在应受刑罚处罚性方面,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目标的盗窃未遂行为仍是应当受到刑事打击的目标。因此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目标的盗窃未遂行为,依然符合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犯罪中的一种形态,应当给予刑事上的追究。再从法理角度讲,司法解释应当合法,对本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目标的未遂盗窃犯罪行为以司法解释形式规定不予追究,实际上是违反立法本意的,因为刑法第264条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即应当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出罚金,这是对盗窃既遂的处罚,那么对以数额较大公私财物为目标的盗窃未遂行为则可以比照盗窃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不能不处罚或不作为犯罪追究。另一角度看,对盗窃数额较大的既遂行为予以处罚(依刑法264条),对盗窃数额较大的未遂行为不处罚(依前述规定),也恰恰证明了该款规定的违法性(违反刑法23条)。 另外,《解释》的此项规定客观上会给未遂的犯罪分子留下逃避法律制裁的空间,因为相当一部分盗窃案件的行为人在盗窃作案的初期并无明确的目标,有的是见什么偷什么,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审理时对其主观故意是很难查清的,因为行为人为了逃避处罚,往往避重就轻,即使本来是以某一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案发后也会隐瞒这一犯罪目的,说成是以某一数额较大之财物为盗窃目标,从而达到逃避处罚的目的。由此造成此类型的盗窃未遂案件与其他类型犯罪未遂(如抢劫未遂)案件在处理上的反差(其他类型的未遂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以犯罪予以处理的),从而造成执法的不统一。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废止《解释》的此项规定,统一执行刑法中对未遂犯罪的处罚原则,即对于那些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因意志以外的原因盗窃未遂的行为人,仍应当按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定罪处罚,并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切实改变盗窃未遂不受刑罚处罚的现状,尽可能的杜绝人为的放纵犯罪的现象。当然,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的盗窃数额未达到较大的未遂行为人不应作犯罪处理。 二、关于对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次数的认定问题 刑法264条将“多次盗窃”作为构成盗窃罪的另一种基础要件,是以次数而非数额认定犯罪的一种形式,也是对刑法取消惯窃罪后的一个有益补充。对什么是“多次盗窃”,刑法本身未作规定,《解释》第4条则作了明确,即“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此条将多次盗窃地点限定为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盗窃次数限定为三次以上。实践中对“三次”如何理解则出现了一点分歧,比如:一年内入户盗窃二次,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累计盗窃三次以上,是否构成盗窃罪,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必须是入户盗窃三次以上或者是扒窃三次以上的才能构成犯罪,因此前例不构成犯罪。这种理解是否正确?笔者以为,我们执行法律必须深入研究其内涵,把握其立法原意,才能作出准确的理解。刑法之所以将“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开场所扒窃三次以上”规定为可以构成盗窃罪,主要是从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角度考虑的,一方面是从数额上将数额较大规定为犯罪,一方面是从次数的量上规定什么是犯罪。此规定将次数的多与少作为罪与否的依据,因此就不能将“入户盗窃”与“在公共场所扒窃”的次数片面理解为均需“三次以上”,在两种盗窃地点只要作案次数达到三次,就说明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较深,社会危害也较大,所以有必要给予刑事处罚。作为司法实务指南的司法解释应当最大限度地体现法律的初衷和内涵,力求准确、严谨,以避免司法实务中引发歧义。因此建议对《解释》第4条进一步明确,具体可表述为“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累计达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有一次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则应另当别论,不以次数为限了。 三、关于对多次盗窃行为数额的认定问题 前文已述,对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的以次数多少而非数额多少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但对行为人的处罚轻重将要涉及其盗窃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大量的并非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或不是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的多次盗窃行为和多种盗窃形式。对这些多次盗窃行为如何认定犯罪数额的问题,实践中也多有争论。如行为人几年里多次实施盗窃,其中每一起盗窃数额均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累计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或者行为人多次实施盗窃,只有其中一次盗窃行为构成犯罪,对盗窃行为人多次盗窃的数额应否累计计算等。对此,《解释》第5条第12项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之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根据此解释,对在一年内三次以上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构成犯罪的数额以累计计算无疑;对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之内的,亦应累计计算无疑。但是对不属于这两种情形的多次盗窃行为如何累计数额该解释似乎不太明确,比如:某行为人案发时的盗窃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其在一年内的另外一起盗窃行为已构成犯罪,那么在计算其盗窃数额时应否累计其案发行为的数额?再如,案发时的行为未构成犯罪,但其在一年前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盗窃数额应否累计等?这一解释还有一些其他值得推敲之处:(一)“多次盗窃构成犯罪”是否是指每次盗窃都构成犯罪?联系该条规定的前后意思,似乎应该理解为每次都构成犯罪(因为只有犯罪才使用追诉的字眼),那么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多次盗窃行为,由于每次单独的盗窃数额都没有达到较大的起点,根据此规定就不能对这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这类盗窃现象在当前十分突出,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社会危害也是十分显著的,这一矛盾不处理,社会秩序将不能得到真正的好转。比如当前在农村一些地区,盗窃家禽家畜的现象十分突出,而就其每一次的盗窃数额来说,并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也就是说每次都不构成犯罪,但是行为人往往在多年内数十次作案,盗窃数额达数千元以上,如果这样的行为得不到刑罚的处罚,恐与立法的初衷相违背。(二)此解释与刑法对其他犯罪的多次行为的有关规定不尽一致,例如,刑法第383条第2款规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又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6日《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4)项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未经行政处罚处理,依法应当追诉的,抢夺数额累计计算。”上述规定既无每次行为均要独立构成犯罪的要求,也无前后两次行为时间的限制。这种对于“多次行为”在处理上认定的不一致导致执法尺度的不统一,并造成处罚上的宽严不均;(三)如果对每次盗窃数额累计计算,那么有无时间的限制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比如对已案发的行为人在10年、20年前的小额盗窃是否亦应累计?等等,在刑法未作修改的前提下,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最高院通过解释形式予以明确化。 四、关于对盗窃累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解释》第6条第(3)项规定的精神,当行为人“盗窃数额较大”并是累犯时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当行为人“盗窃数额巨大”并是累犯时应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按照刑法264条规定,对上述两种情节的行为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幅度之内量刑。换言之即,如果行为人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达到较大,依刑法264条规定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或单处罚金,但如果同时属于累犯,那么就需上升一个格次在3年以上10年以下量刑幅度内决定刑罚。当盗窃数额达到巨大同时又是累犯的也同样上升一个格次在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幅度内决定刑罚。显然,《解释》对于累犯犯盗窃罪采用的是“加重处罚”原则,这也是目前司法解释中看到的唯一对累犯加重处罚的规定。然而,《解释》这样的规定与《刑法》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相悖之处。《刑法》第65条规定,对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第62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这两条规定体现的是“累犯从重”原则,显然,《解释》对累犯处罚的规定违背了刑法的原意,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重复使用了量刑情节,加重行为人的刑罚负担。如某行为人系累犯,盗窃财物价值11000元,按照《解释》的第3条规定,11000元属于“数额巨大”的情节(第3条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至20000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按照刑法264条、62条、65条之规定,本应该在3到10年的幅度内从重,但如果按照《规定》第6条第3项的规定,就必须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幅度内量刑,甚至还要在此基础上从重(即既加重又从重),这种盗窃11000元就要判处10年以上刑罚的处罚结果明显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影响了犯罪分子的悔罪和改造。而事实上《解释》这一畸重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并不能得到执行。为了保证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实施,维护刑法在实施中的权威,在刑法未修改的前提下,不能以前述的解释改变刑法的规定,变相的加重犯罪人的刑罚负担,因此建议最高院对该条款予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