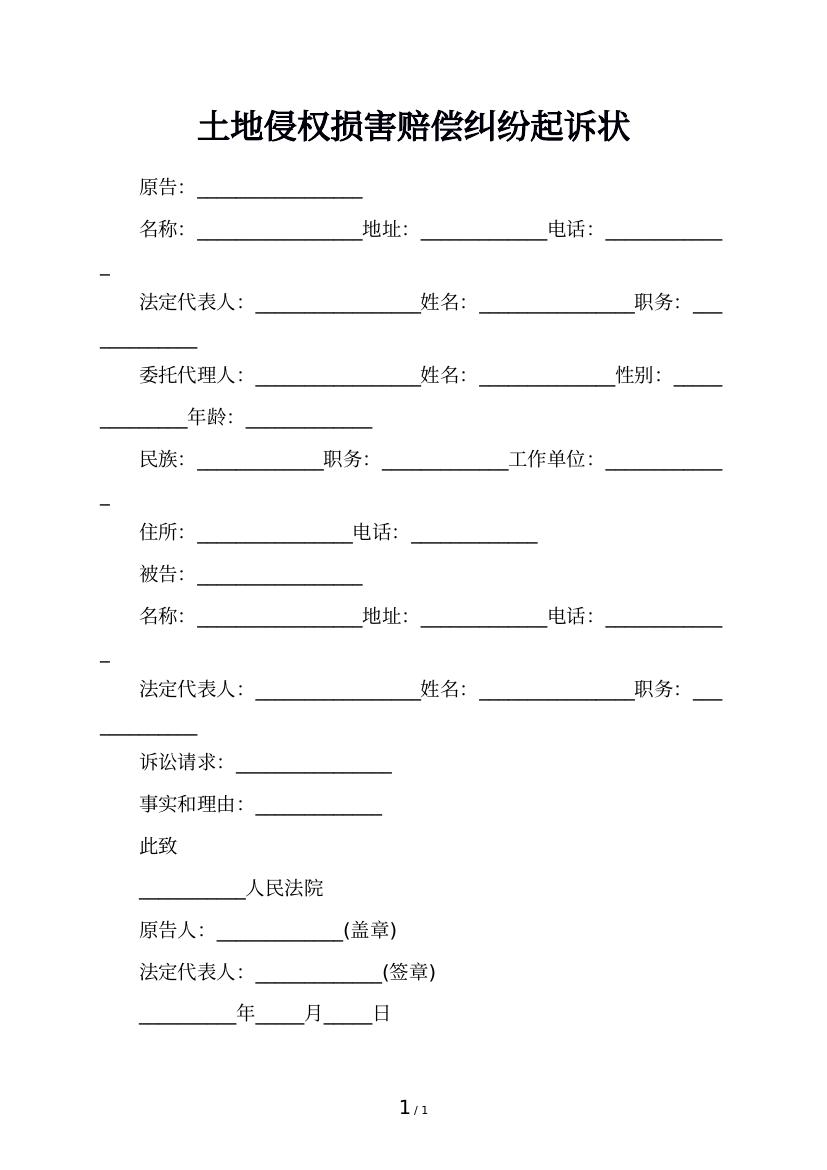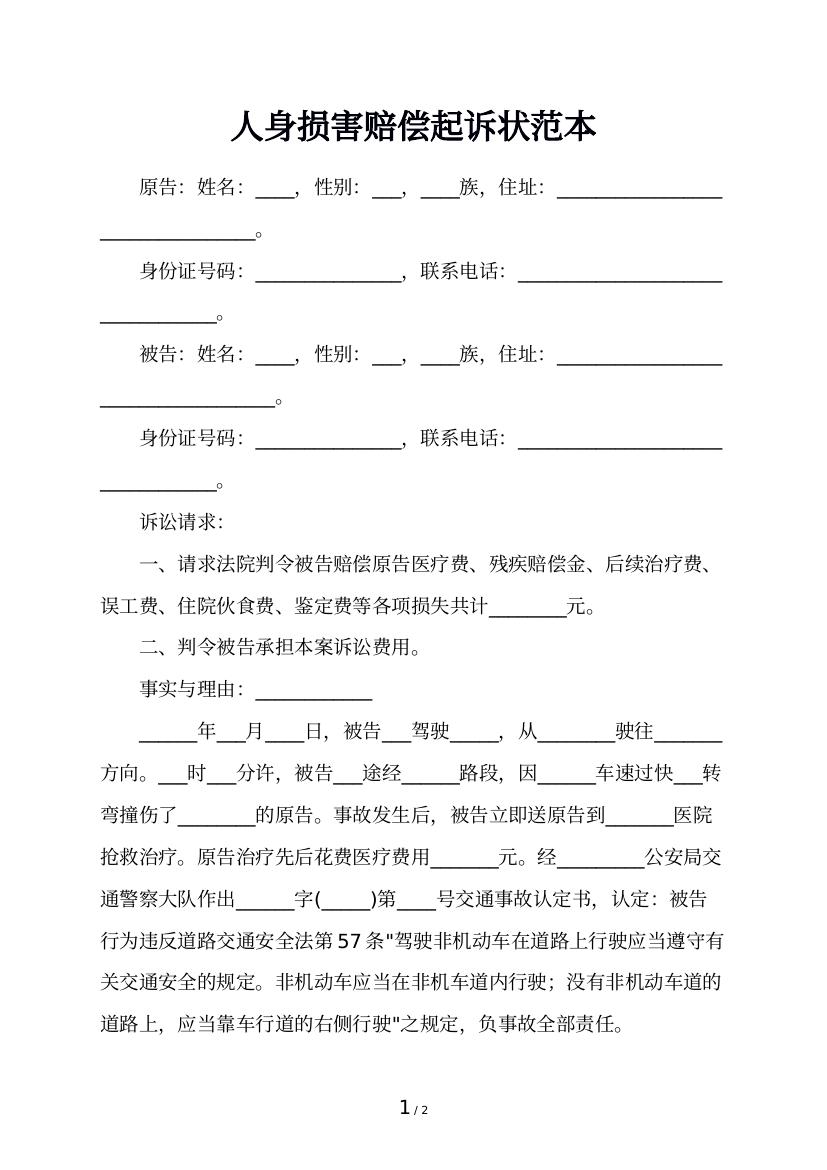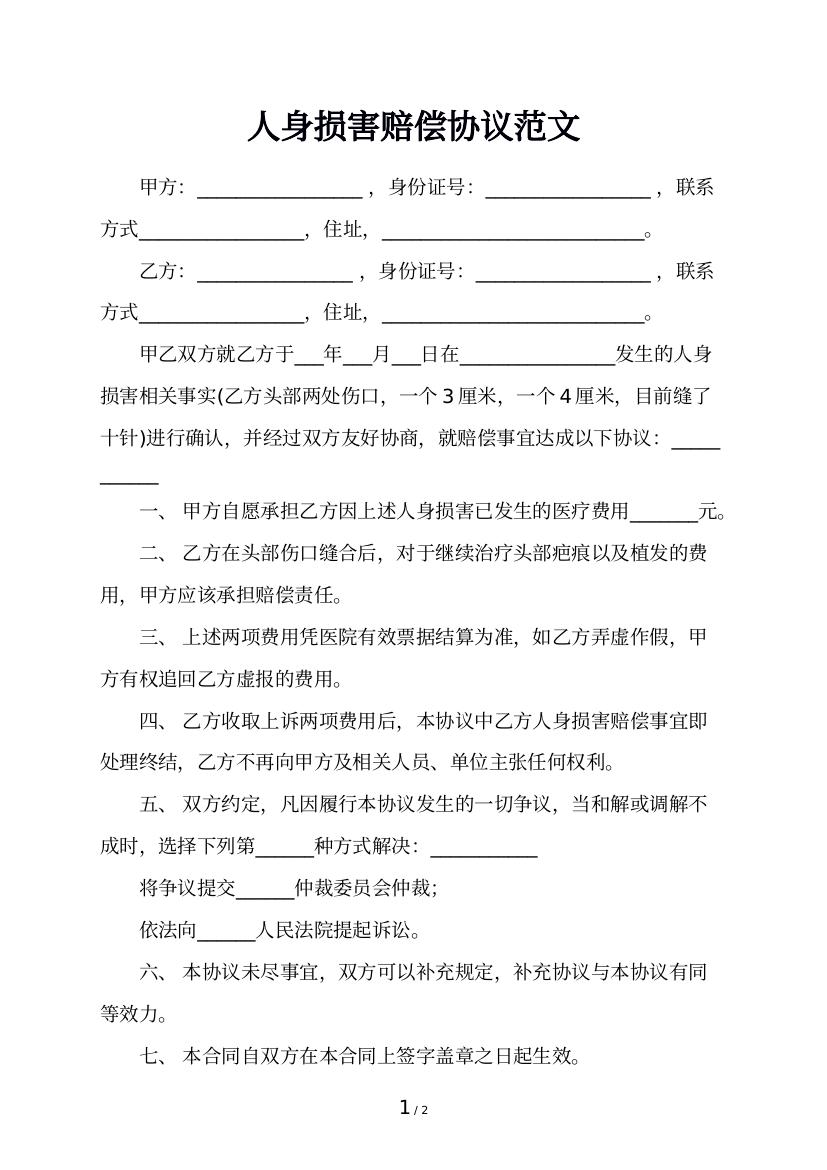国际航空法中的旅客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讨
2019-06-19 07:53
找法网官方整理
导读:
国际航空法中的旅客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讨何祥菊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范围如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承运人的责任到底包不包括精神损害,尤其
国际航空法中的旅客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讨
何祥菊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范围如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承运人的责任到底包不包括精神损害,尤其是纯粹的精神损害争论不休。国际航空运输事故可能会产生三种类型的精神损害。第一种是不伴有身体伤害的纯粹的精神损害(pure mental injury/mental injury unaccompanied by physical injury),第一种是航空事故导致的身体伤害而引起的精神损害(mental injury caused by physical injury),第三种是航空事故造成精神痛苦而引起了身体伤害(Physical injury caused by mental injury)。在后两种情形中,精神损害伴有身体伤害(mental injury accompanied by physical injury)。
一、华沙体系
目前在国际航空私法中,适用最广泛的是1929年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华沙公约》)。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华沙公约经历了数次修订。随后的修订文件主要有1955年的《海牙议定书》、1961年的《瓜达拉哈拉公约》、1971年的《危地马拉议定书》和1975年的四个《蒙特利尔议定书》。《华沙公约》第17条是航空承运人赔偿责任的核心条款,其规定为:“旅客因死亡、受伤或受到其他任何身体伤害(death or wounding of a passenger or any other bodily injury),如果造成这种损失的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登机或下机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承运人应负责任。”从这条的文字表述来看,承运人的责任似乎严格限制在身体伤害的范围内。法文文本是《华沙公约》的唯一正式文本,其所使用的术语是“en cas de mort,de blessure on tout autre lesion corporelle subie”。《华沙公约》的两个英译本均译做“bodily injury”。华沙会议记录显示,当时对使用这个词没有做任何讨论。德国出席华沙会议的代表、著名航空法专家里泽教授,曾用德语将此语译做“任何对健康的侵害”,并为德国、奥地利与瑞士等国所采纳。较之“人身伤害”,里泽的译法更有可能解释为包括精神创伤。
《海牙议定书》和《危地马拉议定书》的英文本(正式文本)均使用“人身伤害”取代了“身体伤害”。显然“人身伤害”比“身体伤害”的范围广,涵盖了精神损害。这两个议定书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认可了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华沙体系用语的混乱和各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加剧了这一争论,也给各国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
二、美国的司法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航空运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华沙公约》的缔约国。司法实践遇到了大量关于国际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案件。美国法院对于国际航空旅行中可能产生的三种类型的精神损害均有判例,尤其在旅客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判例。
(一)纯粹的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在Eastern Airlines Inc.V.Floyd案之前,对于纯粹的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美国法院的有关判例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在lesion corporelle一语的涵义、公约的起草历史。公约起草者的意图、如何更好地实现公约的立法宗旨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即使是持相同结论的判例,其分析推理也并不完全相同。
1.《华沙公约》第17条不包括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
(1)Burnett v.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1970年9月6日,四架从欧洲到纽约的大型客机被劫,在美国引起了几宗著名的民事诉讼案。这些案件的原告大多是犹太妇女和儿童,她们在劫机过程中受到了惊恐等剧烈精神刺激,导致神经质、脾气暴躁。失眠梦魇等。Burnett v.TWA是其中的一个案件。诉讼的焦点集中到《华沙公约》第17条的“身体伤害”是否包括精神损害。法院认为公约第17条不涉及纯粹的精神损害,其理由如下:法文是公约的原始语言,lesion corporelle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支配第17条的解释。法国学者明确区分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害,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害相互排斥,公约使用“身体伤害”一语就排除了精神损害。《华沙公约》的前身是1925年在巴黎起草的一个议定书,这一议定书后来由一个法律专家小组进行了修改,加入了“在死亡、受伤或任何其他身体伤害”。修改后的条文与《华沙公约》第17条几乎完全一样。与修改前的议定书草案相比,《华沙公约》允许赔偿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身体伤害的范围内,排除了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
(2)Rosman v.Trans World Airlines,Inc.
Rosman v.TWA是上文提到的劫机引发的案件之一。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认为精神损害不可以获得赔偿。但与Burnett一案推理不同的是,法院认为lesion corporelle一语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与案件无关,虽然公约以法文文本为准,但对第17条的翻译没有争议,因此法院并不考虑翻译问题。案件的焦点集中在“身体伤害”一语的通常涵义上。法院认为“身体伤害”的涵义是“可见的明显的身体伤害”,不包括没有身体表现只有行为表现的精神伤害。此外,法院认为狭义解释“身体伤害”也有助于促进公约实现法律统一的目的。
2.《华沙公约》第17条包括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
(1)Husserl v.Swiss Air Transport Co.
Husserl v. Swiss Air Transport Co是给予纯粹精神损害的标志性判例。与Rosman案分析相同的是,法院认为美国和其他所有的公约签字国一样,都遵守公约的法文文本,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法院应该受“lesion corporelle”一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的约束,bodily injury是对lesion comorelle的正确翻译。与Rosman案分析不同的是,法院认为“死亡、受伤和任何其他身体伤害”的通常涵义与精神损害相关。法院做出这一解释基本上依赖的一个前提是精神反应和功能是身体的一部分。法院认为公约没有提到精神损害是一种空白,对其做广泛的解释使之包括纯粹身体伤害以外的其他损害是恰当的。“身体损害”一语实际上涵盖了精神损害。
(2)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
另外一个给予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是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与Husserl案分析不同的是,法院认为公约反映的是一种民事责任制度,应该依据“lesion corporelle”一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给予判决,把lesion corporelle直译为bodily injury没有完全抓住该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personal injury则能更好地传达该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此外,法院还认为法国法律并不禁止对特定类型的损害包括精神损害给予赔偿。关于公约起草者的立法意图,法院认为第17条的用语表明立法者没有意图排除某一特定类型的损害,因为如果起草者意欲排除精神损害,就不会将“受伤”这~特定种类的身体伤害单独列出。 [page]
3. Eastern Airlines,Inc.v.Floyd及其随后的判例
(1)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
上文中提到的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一案判决后,Eastern Airlines,Inc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91年4月17日做出判决,认为公约第17条不包括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从而结束了对公约第17条是否包括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长久争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公约的原始文本是法语,lesion corporelle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对解决各方的共同期待具有指导性作用,lesion corporelle的涵义与bodily injury相一致。法院认为其所查阅的相关法国法律资料显示在1929年,虽然法国法律已经对纯粹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但这一信息并不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一般原则,法国没有立法、司法判决和学者著作认为lesion corporelle的法律涵义包括精神痛苦。而且法院认为把lesion corporelle翻译为bodily injury符合公约的谈判历史。当时,许多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不承认纯粹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因此签字国没有将精神损害纳入公约的明确意图,如果立法者明确打算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他们就会明确提及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分析了《华沙公约》的目的。与Husserl案推理相反的是,法院认为对第17条做狭义的解释可以更好地实现公约的首要目标——限制承运人的责任以促进当时还十分脆弱的商业航空的发展。最后,法院提到了《伯尔尼公约》和1929年之后公约签字国的行动。法院认为《蒙特利尔协议》并不支持广义解释第17条,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蒙特利尔协议》旨在修改第17条,而且它是一个协定而不是一个公约。至于《危地马拉议定书》,法院认为其并没有使《华沙公约》意图的范围清楚,尤其是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批准该议定书。
(2)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
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的判决结束了美国法院多年的争论。该案判决在随后的Terrafranca v.Virgin Atlantic Airways,Ltd案中得到遵循。在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案之后,诉讼的焦点转移到什么类型的精神伤害实际构成了身体伤害,由于这些类型的精神伤害在身体中留下了痕迹。在1999年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一案中,原告并没有主张第17条包括精神损害,而是声称其遭受的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一种身体伤害。蒙特纳州地方法院支持了她的主张,认为飞行中发生的事故对她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生理化学反应,这对原告的大脑和神经造成了身体性的影响。虽然法院也承认,依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华沙公约》禁止给予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虽然Weaver所受伤害的表现与以前其他案件中不给予赔偿的伤害的表现类似,然而,本案的中心因素不是法律,而是医学。本案的法律问题仅仅是《华沙公约》是否允许对这种特定类型的身体损害——脑部伤害(即使只有轻微的身体影响)给予赔偿。法院认为这一判决不会为与weaver提出的类似请求打开诉讼大门,因为Weaver的请求是建立在明确诊断基础上的。只有恐惧不能获得赔偿,由恐惧导致的脑部伤害可以获得赔偿。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具有重要意义。长久以来司法界一直认为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是完全不同的,该判决明确承认这两者之间存在联系,总体上挑战了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相区别的观点。这一判决提供了一种方法,凭借此方法,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判例如Floyd将被绕开。2002年,该判决被宣布无效。但蒙特纳地方法院的创造性的分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会影响到未来此类案件的诉讼策略。
(二)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案中的判决没有涉及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的问题,其它的案件讨论了这一问题。
1.身体伤害导致的精神痛苦可以获得赔偿
只有很少的几个美国判例涉及到这个问题。虽这些判例都主张狭义解释第17条,但都认为根据第17条身体伤害导致的精神痛苦可获得赔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loyd案中拒绝给与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之一是对纯粹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违背公约保护航空承运人的首要目标。有学者认为对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痛苦给予赔偿也是违背公约保护承运人的目的的。但在Floyd案后,身体损害导致的精神损害仍可得到赔偿。在Alvarez v.American Airlines,Inc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只有对其所遭受的身体伤害近因造成(proximately caused)的精神损害获得赔偿,仅仅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不可以获得赔偿。”这一结论强调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因果关系。与In re Air crash Disaster Near Roselawn,Indiana on October 31,1994案仅要求精神损害伴有身体伤害就给予赔偿存在重要区别。
2.精神痛苦导致的身体伤害可以获得赔偿
涉及这个问题的判例非常有限。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判例只有Rosman v.Trans World Airlines。此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原告的皮疹是由她在航行中经历的恐惧造成和加剧的,那么她可以就皮疹获得赔偿。在原因(事故)和结果(身体伤害)之间存在中间因果环节(精神痛苦),然而中间的因果环节——精神痛苦不可以获得赔偿。法院因此判决航空公司对原告遭受的明显的客观的身体伤害包括劫机引起的心理创伤导致的身体伤害负有赔偿责任。Rosman案的判决没有受到挑战,然而在Alvarez v.American Airlines,Inc案中,法院认为:“如果精神痛苦的表现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可以依据《华沙公约》获得赔偿,由于空气湍流而受到惊吓的乘客就可以以心跳加速为由获得赔偿。那么乘客不能根据《华沙公约》17条就纯粹的精神损害获得赔偿这一规则就变得形同虚设。”法院因此不赞成Rosman的推理,认为由心理因素作为中间环节的身体损害不可以获得赔偿。
上述两个案件判决似乎并不一致,但其核心问题却是:什么是身体伤害,什么样的身体表现可以获得赔偿。
(三)解决问题的另类思路
上面提到的判例都是从《华沙公约》第17条的语义和立法意图的角度分析承运人的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也有判例采取另外一种思路。《华沙公约》第24条规定:“凡属要适用第18条和第19条的案件,任何损害赔偿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只能以本公约规定的条件与期限提出。凡属要适用第17条的案件,上款规定同样适用,但这并不妨碍对于谁是有起诉权的人以及他们各自有那些权利等问题的确定。”显然,公约第17条受第24条的限制,公约第24条表明公约不影响谁有权提起诉讼和什么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而是把它们留给案件受理法院所在国的国内法解决。19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的判决中认为公约第24条允许根据国际私法规则而适用的国内法决定什么损害可以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赔偿的问题。如果适用于案件的国内法认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原告就可以要求航空公司赔偿精神损害。这一判决依据《华沙公约》第24条,引进国际私法的方法,将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留给国内法决定。 [page]
三、英国的司法实践
英国贵族院最近合并审理了两起涉及航空旅行乘客精神损害赔偿的上诉案件,一个案件是Morris v.KLM Dutch Airlines,另一个案件是King v.Bristow Helicopters Ltd。这两起案件诉讼的焦点都是航空旅客由于航空事故而遭受到精神伤害是否可以要求赔偿。最基本的问题是对“身体伤害”的解释。关于对公约解释的方法,贵族院认为由于国际公约旨在国际层面上统一责任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法院的解释必须与其他法域的解释相~致,而且公约必须根据达成公约当时的理解进行解释。
贵族院回顾了公约的准备文献和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各国法院对公约第17条的解释,特别参考了美国法院Eastern Airlines Inc v.Floyd的判决。贵族院认为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判例都将第17条可以赔偿的范围限制在“死亡、身体伤害和有身体表现的伤害”从而排除了纯粹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贵族院认为即使不考虑这些判例,由于下述理由,纯粹的精神损害仍然不可以获得赔偿。《华沙公约》签订于1929年,那时几乎没有法律制度对事故中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公约的目的之一是给予新生的航空运输一定程度的保护,如果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就会为许多额外的诉讼打开大门,这与保护航空承运人的目的不一致。鉴于航空运输中有很多因素可以引起乘客震惊、焦虑。沮丧、痛苦、恐惧等精神反应,主张采用严格责任的《华沙公约》意图包括这些项目是不合理的。此外,“身体伤害”一词的通常涵义是指对身体结构造成的生理伤害,与精神损害形成鲜明对比。对于1929年之后,医学发展对损害赔偿的影响,贵族院在判决中承认“如果原告可以证明大脑受到损害,且第17条规定的其他赔偿条件满足,却依然坚持认为,在1929年,精神损害是无法证明的就拒绝给予赔偿是不正确的”。
这两起案件清楚地表明了英国贵族院对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拒绝给予纯粹精神损害救济,对于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贵族院认为可以获得赔偿。“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可能联系在一起。‘身体伤害’是《华沙公约》的门槛性要求(threshold requirement),不论是事故导致的精神损害引起了身体伤害比如中风、流产、胃溃疡等,还是航空事故中造成的身体伤害而引起的精神痛苦,这一门槛性要求都是满足的”。
比较美国和英国法院的实践可以看出两国法院都强调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尤其是英国法院在判决时参考其他国家法院的判例,两国最高司法机构对于三种精神损害类型是否可以获得赔偿基本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院这方面的实践和思路极其活跃,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和Weaver v.Delta Airlines的判决都非常富有创造性,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未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的诉讼和判决具有启发和影响的作用。
四、中国的司法实践
中国是《华沙公约》的签字国之一。《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据此,中国法院有适用《华沙公约》的义务,同样面临第17条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难题。
(一)陆红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乘坐被告UA801班机由美国夏威夷经日本飞往香港,该机在日本成田机场起飞时,飞机的左翼引擎发生故障,原告在紧急撤离过程中腿部受伤。在起诉中,原告除要求赔偿伤残损失费、护理费外,还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和美国都是《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的成员国,因此本案适用《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侵权为由在判决中责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显然,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是由身体伤害导致的,判决对这种情形的精神损害采取了认可的态度,但是没有说明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否法院认为《华沙公约》第17条包括精神损害而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主张不得而知。这不能不算本案判决的一大遗憾,大大减损了该案的指导性意义,但就其实体结果而言仍具有意义,“此案在处理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时,适用了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为我国法院今后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案中,原告的精神损害是由身体伤害造成的,对于纯粹精神损害和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引起的身体损害是否可以得到赔偿,我国法院至今还没有案例涉及。
(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确认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解释》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只有特定权利遭受侵害时,受害人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同时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只是侵害精神损害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只有当侵权人承担其他形式的民事责任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况下,方可考虑采取金钱赔偿的方式。
可以预计《解释》对我国关于国际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的影响是间接的。因为与我国有国际航空运输路线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华沙公约》的缔约国。一旦发生旅客损害赔偿纠纷,《华沙公约》将优先适用。为了实现《华沙公约》在国际层面上统一规则的目标,中国法院可能会考虑其他国家的有关判例,而采用国内法的观点解释国际公约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即使中国法院不纠缠于《华沙公约》第17条的解释,而采用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的思路,通过冲突规范的指引找到准据法,即使拮据法是中国法,根据《解释》,没有某种权利或利益受到损害,单纯的精神损害不可以赔偿。
由于中国国际航空运输起步较晚,目前涉及国际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非常有限,对《华沙公约》第17条解释的探讨几乎一片空白,更谈不上对航空精神损害赔偿加以类型化的研究。但随着中国国际航空运输的发展,这类案件将不可避免地涌现,国外积累的丰富判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解释》允许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非常狭窄,这和整个中国法律发展水平低直接相关。只有随着中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承认纯粹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若在国际航空事故中采用Zicherman v. Korean Airlines Co思路而适用中国法,旅客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要求才能得到法院支持。
五、《蒙特利尔公约》
为了在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CAO)框架内,发展一套机制以加速华沙体系的现代化和统一性,ICAO在综合《华沙公约》等11个有关国际航空的运输文件的基础上,1999年推出了新的《统一国际航空运动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在1999年国际民航组织航空私法外交会议上通过,目前还未生效。由于条约只对缔约方有约束力,即使在《蒙特利尔公约》生效后,并不意味着原有华沙体系全部文件就废止,而是在缔约国之间仍然有效。尽管《蒙特利尔公约》第55条规定其优先于其他《华沙公约》文件,但只要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批准加入,多个公约文件并存适用于国际航空运输的局面就将继续存在。 [page]
承运人的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是起草《蒙特利尔公约》时争论的焦点之一。公约草案第一稿第16条明确把精神损害纳入了赔偿范围。该草案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经过了进一步修改,引进“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的概念以涵盖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但这一建议在蒙特利尔外交会议上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审查了研究小组的报告后,保留了“精神损害”,然而在交给1999年5月外交会议的最终草案中,“人身伤害”和“精神伤害”都被删除,只保留了“身体伤害”。
部分成员国试图使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建议对“身体伤害”达成一项解释性声明,根据这一声明,各个法域可以根据国内法的发展状况决定是否给予航空旅客精神损害以赔偿。这种建议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案中的判决的思路非常相似。但有代表认为这种用国内法的发展来改变公约术语涵义和范围的方法是不恰当的,结果不了了之。
对于《蒙特利尔公约》仍然坚持使用“身体伤害”一词,有学者认为这事实上给了法院明确指示:《蒙特利尔公约》在立法意图上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可以赔偿的范围之外。但也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将精神损害与有形的身体损害相联系的趋势,从医学的角度看,越来越难以把精神损害同身体损害分离开来,二者经常纠缠在一起,精神损害实际是一种身体损害,精神损害包含在身体伤害之中。将“精神损害”从《蒙特利尔公约》中删除并不能简单地得出精神损害不可赔偿的结论。因此,即使《蒙特利尔公约》生效。关于承运人的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并没有完结,仍然将持续下去。
六、结 论
国际航空事故可能给旅客造成非常严重的精神痛苦,以致严重损害日常生活能力,这时有没有外部的身体伤害已经不重要了。法律的任务就是给予损害应得的救济。如果损害和事故有因果关系,毫无疑问,这种损害应该得到赔偿。目前,许多国家的国内法都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应该在《华沙公约》中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适当的位置。其次,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精神损害的本质不仅应从法律的角度也应该从医学的角度考虑。从法律的角度讲,法官先入为主地认为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有严格的区别,把法文本的“lesion corporelle”严格地解释为身体伤害更加剧了这种误解。从医学角度看,精神损害的根源是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会导致身体发生变化。精神损害本质上是一种身体损害,没有必要再为华沙公约是否涉及精神损害而争论不休。对国际航空旅行中可能产生的三种类型的精神损害尤其是纯粹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应该是国际航空法发展的趋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法学院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Singed at Warsaw on 12 October 1929(hereinafter Warsaw Convention),at http://www.jus. uio. no/lm/air.carriage. warsaw. convention. 1929/doc. html,art.17(emphasis added),last visited May 13,2003.
赵维田著:《国际航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Guatemala City Protocol 1971,at.http://www.fog.it/convenzioni/inglese/guatemala-1971.htm,art.17(emphasis added),last visited May 13,2003.
“Personal injury”的涵义是“非财产损害,而是对身体、心理或感情的伤害。比如如果你在杂货店踩到香蕉皮而跌倒,遭受的人身伤害包括实际的身体伤害和在公众面前跌倒时感到的羞辱,但是摔碎的手表不包括在内”(An injury not to property,but to your body,mind or emotions.For example,if you slip and fall on a banana peel in the grocery store,personal injury covers any actual physical harm(broken leg and bruises) you suffered in the as well as the humiliation of falling in Public,but not the harm shattering your watch),at http://www. nolo.com/lawcenter/dictionary/dictionary_listing. cfm/Term/DEEEOE11-E3A5-4E2D-9E36FA5CC1F46D61/alpha/P,last visited May 28,2003.
See Burnett v.Trans World Airlines,Inc.368 F.Supp.1152,(D. N. 1973),参见赵维田著:《国际航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See Rosman v.Tran。World Airlines,Inc.34 N.Y.2d 385(N.Y.A.1974).
See Husserl v. Swiss Air Transport Co,351 F.Supp.702(S.D.N.Y.1972),see also Ruwantissa I.R.Abeyratne,Mental Distress Aviation Claims-Emergent Trends,65 J. Air L. & Com. 227 (2000).
See 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 872 F.2d 1462(11th Cir.1989).
See Eastern Airlines,Inc v Floyd,499 U. S. 530(1991),又见黄力华:《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从〈华沙公约〉到〈蒙特利尔公约〉》,载《民商法论丛》(第20卷),金桥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79-280页。
但有学者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推理完全忽略了“lesion corpoprelle”该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虽然lesion corporelle没有特别包括精神损害,但也没有特别证据表明该词特别排除精神损害。这一判决过分强调许多普通法系国家在1929年不承认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法院的这种分析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普通法系区分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法国民法没有相应的概念,不区分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对于任何一种损害都给予赔偿,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借用普通法系的观点来分析以法文为正式文本的公约是不妥当的。其实法院的主要担心在于如果采用广义解释,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华沙公约》限制承运人责任、促进商业航空运输发展的目标就会受到打击。See J.Brent Alldredge,Continuing Questions in Aviation Liability Law: Should Article 17 of the Warsaw Convention Be Construed to Encompass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Emotional and Mental Distress,67 J.Air L.& Com.1360-1362(2002).
See 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56 F.Supp2d.1190(D.Mont.1999).
See Terrafrance v.Virgin Atlantic Airways,Ltd,151 F. 3d 108(3d Cir.1998). [page]
Alldredge,See J.Brent Alldredge,Continuing Questions in Aviation Liability Law:Should Article 17 of the Warsaw Convention Be Construed to Encompass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Emotional and Mental Distress,67J. Air L.& Com.,at 1366.
See 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211 F Supp.2d1252(D.Mont.2002).
See Alvarez v.American Airlines,Inc,No.98 Civ.1027,1999 WL 69129922,at*5(S.D.N. Y.Sept.7.1999).
In re Air crash Disaster Near Roselawn,Indiana on October 31,1994,法院认为Floyd案仅要求具体伤害是责任的前提要件,一旦这个前提条件满足,Floyd案并不明确禁止精神损害赔偿。此外,法院认为第17条仅明确要求损害和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没有暗示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才可以获得赔偿。虽该案中的精神损害不是由身体损害引起的,法院对遇难乘客遭受的恐惧仍给予了赔偿。
Larsen,Regime of Liabilit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Air Law-with Focus on the Warsaw system and the Montreal Convention of 28 May 1999,at http://www.rettid.dk/artikler/speciale-20020002.pdf,p33,last visited May 24,2003,at 38.
Article 24 of Warsaw Conventioin states: “In the case covered by Article 18 and 19 any action for damages,however founded,can only be brought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s set out in this conventiion. 2 in the case covered by Article 17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oceeding paragraph also apply,without perjudice to questions as to who are the persons who have the right to bring suit and what are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Warsaw Convention,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Singed at Warsaw on 12 October 1929 (hereinafter Warsaw Convention),at http://www.jus.uio.no/Im/air. carriage. warsaw. convention. 1929/doc. html,art. 17(emphasis added),last visited May 13,2003,art.24.
See Zicherman v·Korean Air Lines;516 U.S.217(1996),revg in part,43 F. 3d 18 (2d Cir. 1994).
See King(AP)(Respondent)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 (Appellants)(Scotland)In Re M(A Child by Her Litigation Friend CM)(FC)(Appellant),see also 8 Aviation,International Law Update 52-55(2002).
具体案情参见Morris v.KLM Dutch Airlines EWCA Civ 790(2001).
具体案情参见King 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 1 Lloyd's Rep 95(2001).
See King(AP)(Respondent) 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Appellants)(Scotland)In Re M(A Child by Her Litigation Friend CM)(FC)(Appellant).
《陆红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4期。
参见高万泉、丁小燕:《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载《法学》2002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2001年2月26日。
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2000-2001年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民事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 (hereinafter Montreal Convention),May 28,1999,ICAO Doc 9740.
参见唐明我:《新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责任制度及其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See Husserl v.Swiss Air Transport Co.,351 F.Supp.702(S.D.N.Y.1972),see also Ruwantissal. R.Abeyratne,Mental Distress Aviation Claims-Emergent Trends,65 J.Air L.&Com.227(2000),at 226.
See Husserl v.Swiss Air Transport Co.,351 F.Supp.702(S.D.N.Y.1972),see also Ruwantissal. R.Abeyratne,Mental Distress Aviation Claims—Emergent Trends,65 J.Air L.&Com.227(2000),at 257-258.
何祥菊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范围如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承运人的责任到底包不包括精神损害,尤其是纯粹的精神损害争论不休。国际航空运输事故可能会产生三种类型的精神损害。第一种是不伴有身体伤害的纯粹的精神损害(pure mental injury/mental injury unaccompanied by physical injury),第一种是航空事故导致的身体伤害而引起的精神损害(mental injury caused by physical injury),第三种是航空事故造成精神痛苦而引起了身体伤害(Physical injury caused by mental injury)。在后两种情形中,精神损害伴有身体伤害(mental injury accompanied by physical injury)。
一、华沙体系
目前在国际航空私法中,适用最广泛的是1929年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华沙公约》)。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华沙公约经历了数次修订。随后的修订文件主要有1955年的《海牙议定书》、1961年的《瓜达拉哈拉公约》、1971年的《危地马拉议定书》和1975年的四个《蒙特利尔议定书》。《华沙公约》第17条是航空承运人赔偿责任的核心条款,其规定为:“旅客因死亡、受伤或受到其他任何身体伤害(death or wounding of a passenger or any other bodily injury),如果造成这种损失的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登机或下机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承运人应负责任。”从这条的文字表述来看,承运人的责任似乎严格限制在身体伤害的范围内。法文文本是《华沙公约》的唯一正式文本,其所使用的术语是“en cas de mort,de blessure on tout autre lesion corporelle subie”。《华沙公约》的两个英译本均译做“bodily injury”。华沙会议记录显示,当时对使用这个词没有做任何讨论。德国出席华沙会议的代表、著名航空法专家里泽教授,曾用德语将此语译做“任何对健康的侵害”,并为德国、奥地利与瑞士等国所采纳。较之“人身伤害”,里泽的译法更有可能解释为包括精神创伤。
《海牙议定书》和《危地马拉议定书》的英文本(正式文本)均使用“人身伤害”取代了“身体伤害”。显然“人身伤害”比“身体伤害”的范围广,涵盖了精神损害。这两个议定书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认可了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华沙体系用语的混乱和各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加剧了这一争论,也给各国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
二、美国的司法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航空运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华沙公约》的缔约国。司法实践遇到了大量关于国际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案件。美国法院对于国际航空旅行中可能产生的三种类型的精神损害均有判例,尤其在旅客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判例。
(一)纯粹的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在Eastern Airlines Inc.V.Floyd案之前,对于纯粹的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美国法院的有关判例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在lesion corporelle一语的涵义、公约的起草历史。公约起草者的意图、如何更好地实现公约的立法宗旨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即使是持相同结论的判例,其分析推理也并不完全相同。
1.《华沙公约》第17条不包括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
(1)Burnett v.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1970年9月6日,四架从欧洲到纽约的大型客机被劫,在美国引起了几宗著名的民事诉讼案。这些案件的原告大多是犹太妇女和儿童,她们在劫机过程中受到了惊恐等剧烈精神刺激,导致神经质、脾气暴躁。失眠梦魇等。Burnett v.TWA是其中的一个案件。诉讼的焦点集中到《华沙公约》第17条的“身体伤害”是否包括精神损害。法院认为公约第17条不涉及纯粹的精神损害,其理由如下:法文是公约的原始语言,lesion corporelle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支配第17条的解释。法国学者明确区分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害,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害相互排斥,公约使用“身体伤害”一语就排除了精神损害。《华沙公约》的前身是1925年在巴黎起草的一个议定书,这一议定书后来由一个法律专家小组进行了修改,加入了“在死亡、受伤或任何其他身体伤害”。修改后的条文与《华沙公约》第17条几乎完全一样。与修改前的议定书草案相比,《华沙公约》允许赔偿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身体伤害的范围内,排除了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
(2)Rosman v.Trans World Airlines,Inc.
Rosman v.TWA是上文提到的劫机引发的案件之一。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认为精神损害不可以获得赔偿。但与Burnett一案推理不同的是,法院认为lesion corporelle一语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与案件无关,虽然公约以法文文本为准,但对第17条的翻译没有争议,因此法院并不考虑翻译问题。案件的焦点集中在“身体伤害”一语的通常涵义上。法院认为“身体伤害”的涵义是“可见的明显的身体伤害”,不包括没有身体表现只有行为表现的精神伤害。此外,法院认为狭义解释“身体伤害”也有助于促进公约实现法律统一的目的。
2.《华沙公约》第17条包括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
(1)Husserl v.Swiss Air Transport Co.
Husserl v. Swiss Air Transport Co是给予纯粹精神损害的标志性判例。与Rosman案分析相同的是,法院认为美国和其他所有的公约签字国一样,都遵守公约的法文文本,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法院应该受“lesion corporelle”一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的约束,bodily injury是对lesion comorelle的正确翻译。与Rosman案分析不同的是,法院认为“死亡、受伤和任何其他身体伤害”的通常涵义与精神损害相关。法院做出这一解释基本上依赖的一个前提是精神反应和功能是身体的一部分。法院认为公约没有提到精神损害是一种空白,对其做广泛的解释使之包括纯粹身体伤害以外的其他损害是恰当的。“身体损害”一语实际上涵盖了精神损害。
(2)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
另外一个给予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是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与Husserl案分析不同的是,法院认为公约反映的是一种民事责任制度,应该依据“lesion corporelle”一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给予判决,把lesion corporelle直译为bodily injury没有完全抓住该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personal injury则能更好地传达该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此外,法院还认为法国法律并不禁止对特定类型的损害包括精神损害给予赔偿。关于公约起草者的立法意图,法院认为第17条的用语表明立法者没有意图排除某一特定类型的损害,因为如果起草者意欲排除精神损害,就不会将“受伤”这~特定种类的身体伤害单独列出。 [page]
3. Eastern Airlines,Inc.v.Floyd及其随后的判例
(1)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
上文中提到的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一案判决后,Eastern Airlines,Inc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91年4月17日做出判决,认为公约第17条不包括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从而结束了对公约第17条是否包括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长久争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公约的原始文本是法语,lesion corporelle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对解决各方的共同期待具有指导性作用,lesion corporelle的涵义与bodily injury相一致。法院认为其所查阅的相关法国法律资料显示在1929年,虽然法国法律已经对纯粹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但这一信息并不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一般原则,法国没有立法、司法判决和学者著作认为lesion corporelle的法律涵义包括精神痛苦。而且法院认为把lesion corporelle翻译为bodily injury符合公约的谈判历史。当时,许多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不承认纯粹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因此签字国没有将精神损害纳入公约的明确意图,如果立法者明确打算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他们就会明确提及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分析了《华沙公约》的目的。与Husserl案推理相反的是,法院认为对第17条做狭义的解释可以更好地实现公约的首要目标——限制承运人的责任以促进当时还十分脆弱的商业航空的发展。最后,法院提到了《伯尔尼公约》和1929年之后公约签字国的行动。法院认为《蒙特利尔协议》并不支持广义解释第17条,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蒙特利尔协议》旨在修改第17条,而且它是一个协定而不是一个公约。至于《危地马拉议定书》,法院认为其并没有使《华沙公约》意图的范围清楚,尤其是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批准该议定书。
(2)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
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的判决结束了美国法院多年的争论。该案判决在随后的Terrafranca v.Virgin Atlantic Airways,Ltd案中得到遵循。在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案之后,诉讼的焦点转移到什么类型的精神伤害实际构成了身体伤害,由于这些类型的精神伤害在身体中留下了痕迹。在1999年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一案中,原告并没有主张第17条包括精神损害,而是声称其遭受的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一种身体伤害。蒙特纳州地方法院支持了她的主张,认为飞行中发生的事故对她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生理化学反应,这对原告的大脑和神经造成了身体性的影响。虽然法院也承认,依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华沙公约》禁止给予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虽然Weaver所受伤害的表现与以前其他案件中不给予赔偿的伤害的表现类似,然而,本案的中心因素不是法律,而是医学。本案的法律问题仅仅是《华沙公约》是否允许对这种特定类型的身体损害——脑部伤害(即使只有轻微的身体影响)给予赔偿。法院认为这一判决不会为与weaver提出的类似请求打开诉讼大门,因为Weaver的请求是建立在明确诊断基础上的。只有恐惧不能获得赔偿,由恐惧导致的脑部伤害可以获得赔偿。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具有重要意义。长久以来司法界一直认为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是完全不同的,该判决明确承认这两者之间存在联系,总体上挑战了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相区别的观点。这一判决提供了一种方法,凭借此方法,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判例如Floyd将被绕开。2002年,该判决被宣布无效。但蒙特纳地方法院的创造性的分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会影响到未来此类案件的诉讼策略。
(二)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Eastern Airlines,Inc v.Floyd案中的判决没有涉及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的问题,其它的案件讨论了这一问题。
1.身体伤害导致的精神痛苦可以获得赔偿
只有很少的几个美国判例涉及到这个问题。虽这些判例都主张狭义解释第17条,但都认为根据第17条身体伤害导致的精神痛苦可获得赔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loyd案中拒绝给与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之一是对纯粹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违背公约保护航空承运人的首要目标。有学者认为对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痛苦给予赔偿也是违背公约保护承运人的目的的。但在Floyd案后,身体损害导致的精神损害仍可得到赔偿。在Alvarez v.American Airlines,Inc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只有对其所遭受的身体伤害近因造成(proximately caused)的精神损害获得赔偿,仅仅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不可以获得赔偿。”这一结论强调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因果关系。与In re Air crash Disaster Near Roselawn,Indiana on October 31,1994案仅要求精神损害伴有身体伤害就给予赔偿存在重要区别。
2.精神痛苦导致的身体伤害可以获得赔偿
涉及这个问题的判例非常有限。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判例只有Rosman v.Trans World Airlines。此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原告的皮疹是由她在航行中经历的恐惧造成和加剧的,那么她可以就皮疹获得赔偿。在原因(事故)和结果(身体伤害)之间存在中间因果环节(精神痛苦),然而中间的因果环节——精神痛苦不可以获得赔偿。法院因此判决航空公司对原告遭受的明显的客观的身体伤害包括劫机引起的心理创伤导致的身体伤害负有赔偿责任。Rosman案的判决没有受到挑战,然而在Alvarez v.American Airlines,Inc案中,法院认为:“如果精神痛苦的表现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可以依据《华沙公约》获得赔偿,由于空气湍流而受到惊吓的乘客就可以以心跳加速为由获得赔偿。那么乘客不能根据《华沙公约》17条就纯粹的精神损害获得赔偿这一规则就变得形同虚设。”法院因此不赞成Rosman的推理,认为由心理因素作为中间环节的身体损害不可以获得赔偿。
上述两个案件判决似乎并不一致,但其核心问题却是:什么是身体伤害,什么样的身体表现可以获得赔偿。
(三)解决问题的另类思路
上面提到的判例都是从《华沙公约》第17条的语义和立法意图的角度分析承运人的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也有判例采取另外一种思路。《华沙公约》第24条规定:“凡属要适用第18条和第19条的案件,任何损害赔偿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只能以本公约规定的条件与期限提出。凡属要适用第17条的案件,上款规定同样适用,但这并不妨碍对于谁是有起诉权的人以及他们各自有那些权利等问题的确定。”显然,公约第17条受第24条的限制,公约第24条表明公约不影响谁有权提起诉讼和什么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而是把它们留给案件受理法院所在国的国内法解决。19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的判决中认为公约第24条允许根据国际私法规则而适用的国内法决定什么损害可以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是否可以赔偿的问题。如果适用于案件的国内法认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原告就可以要求航空公司赔偿精神损害。这一判决依据《华沙公约》第24条,引进国际私法的方法,将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留给国内法决定。 [page]
三、英国的司法实践
英国贵族院最近合并审理了两起涉及航空旅行乘客精神损害赔偿的上诉案件,一个案件是Morris v.KLM Dutch Airlines,另一个案件是King v.Bristow Helicopters Ltd。这两起案件诉讼的焦点都是航空旅客由于航空事故而遭受到精神伤害是否可以要求赔偿。最基本的问题是对“身体伤害”的解释。关于对公约解释的方法,贵族院认为由于国际公约旨在国际层面上统一责任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法院的解释必须与其他法域的解释相~致,而且公约必须根据达成公约当时的理解进行解释。
贵族院回顾了公约的准备文献和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各国法院对公约第17条的解释,特别参考了美国法院Eastern Airlines Inc v.Floyd的判决。贵族院认为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判例都将第17条可以赔偿的范围限制在“死亡、身体伤害和有身体表现的伤害”从而排除了纯粹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贵族院认为即使不考虑这些判例,由于下述理由,纯粹的精神损害仍然不可以获得赔偿。《华沙公约》签订于1929年,那时几乎没有法律制度对事故中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公约的目的之一是给予新生的航空运输一定程度的保护,如果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就会为许多额外的诉讼打开大门,这与保护航空承运人的目的不一致。鉴于航空运输中有很多因素可以引起乘客震惊、焦虑。沮丧、痛苦、恐惧等精神反应,主张采用严格责任的《华沙公约》意图包括这些项目是不合理的。此外,“身体伤害”一词的通常涵义是指对身体结构造成的生理伤害,与精神损害形成鲜明对比。对于1929年之后,医学发展对损害赔偿的影响,贵族院在判决中承认“如果原告可以证明大脑受到损害,且第17条规定的其他赔偿条件满足,却依然坚持认为,在1929年,精神损害是无法证明的就拒绝给予赔偿是不正确的”。
这两起案件清楚地表明了英国贵族院对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拒绝给予纯粹精神损害救济,对于伴有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贵族院认为可以获得赔偿。“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可能联系在一起。‘身体伤害’是《华沙公约》的门槛性要求(threshold requirement),不论是事故导致的精神损害引起了身体伤害比如中风、流产、胃溃疡等,还是航空事故中造成的身体伤害而引起的精神痛苦,这一门槛性要求都是满足的”。
比较美国和英国法院的实践可以看出两国法院都强调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尤其是英国法院在判决时参考其他国家法院的判例,两国最高司法机构对于三种精神损害类型是否可以获得赔偿基本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院这方面的实践和思路极其活跃,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和Weaver v.Delta Airlines的判决都非常富有创造性,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未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的诉讼和判决具有启发和影响的作用。
四、中国的司法实践
中国是《华沙公约》的签字国之一。《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据此,中国法院有适用《华沙公约》的义务,同样面临第17条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难题。
(一)陆红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乘坐被告UA801班机由美国夏威夷经日本飞往香港,该机在日本成田机场起飞时,飞机的左翼引擎发生故障,原告在紧急撤离过程中腿部受伤。在起诉中,原告除要求赔偿伤残损失费、护理费外,还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和美国都是《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的成员国,因此本案适用《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侵权为由在判决中责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显然,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是由身体伤害导致的,判决对这种情形的精神损害采取了认可的态度,但是没有说明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否法院认为《华沙公约》第17条包括精神损害而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主张不得而知。这不能不算本案判决的一大遗憾,大大减损了该案的指导性意义,但就其实体结果而言仍具有意义,“此案在处理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时,适用了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为我国法院今后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案中,原告的精神损害是由身体伤害造成的,对于纯粹精神损害和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引起的身体损害是否可以得到赔偿,我国法院至今还没有案例涉及。
(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确认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解释》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只有特定权利遭受侵害时,受害人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同时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只是侵害精神损害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只有当侵权人承担其他形式的民事责任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情况下,方可考虑采取金钱赔偿的方式。
可以预计《解释》对我国关于国际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的影响是间接的。因为与我国有国际航空运输路线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华沙公约》的缔约国。一旦发生旅客损害赔偿纠纷,《华沙公约》将优先适用。为了实现《华沙公约》在国际层面上统一规则的目标,中国法院可能会考虑其他国家的有关判例,而采用国内法的观点解释国际公约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即使中国法院不纠缠于《华沙公约》第17条的解释,而采用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的思路,通过冲突规范的指引找到准据法,即使拮据法是中国法,根据《解释》,没有某种权利或利益受到损害,单纯的精神损害不可以赔偿。
由于中国国际航空运输起步较晚,目前涉及国际航空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非常有限,对《华沙公约》第17条解释的探讨几乎一片空白,更谈不上对航空精神损害赔偿加以类型化的研究。但随着中国国际航空运输的发展,这类案件将不可避免地涌现,国外积累的丰富判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解释》允许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非常狭窄,这和整个中国法律发展水平低直接相关。只有随着中国侵权行为法的发展,承认纯粹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若在国际航空事故中采用Zicherman v. Korean Airlines Co思路而适用中国法,旅客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要求才能得到法院支持。
五、《蒙特利尔公约》
为了在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CAO)框架内,发展一套机制以加速华沙体系的现代化和统一性,ICAO在综合《华沙公约》等11个有关国际航空的运输文件的基础上,1999年推出了新的《统一国际航空运动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在1999年国际民航组织航空私法外交会议上通过,目前还未生效。由于条约只对缔约方有约束力,即使在《蒙特利尔公约》生效后,并不意味着原有华沙体系全部文件就废止,而是在缔约国之间仍然有效。尽管《蒙特利尔公约》第55条规定其优先于其他《华沙公约》文件,但只要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批准加入,多个公约文件并存适用于国际航空运输的局面就将继续存在。 [page]
承运人的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是起草《蒙特利尔公约》时争论的焦点之一。公约草案第一稿第16条明确把精神损害纳入了赔偿范围。该草案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经过了进一步修改,引进“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的概念以涵盖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但这一建议在蒙特利尔外交会议上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审查了研究小组的报告后,保留了“精神损害”,然而在交给1999年5月外交会议的最终草案中,“人身伤害”和“精神伤害”都被删除,只保留了“身体伤害”。
部分成员国试图使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建议对“身体伤害”达成一项解释性声明,根据这一声明,各个法域可以根据国内法的发展状况决定是否给予航空旅客精神损害以赔偿。这种建议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icherman v.Korean Airlines Co案中的判决的思路非常相似。但有代表认为这种用国内法的发展来改变公约术语涵义和范围的方法是不恰当的,结果不了了之。
对于《蒙特利尔公约》仍然坚持使用“身体伤害”一词,有学者认为这事实上给了法院明确指示:《蒙特利尔公约》在立法意图上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可以赔偿的范围之外。但也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将精神损害与有形的身体损害相联系的趋势,从医学的角度看,越来越难以把精神损害同身体损害分离开来,二者经常纠缠在一起,精神损害实际是一种身体损害,精神损害包含在身体伤害之中。将“精神损害”从《蒙特利尔公约》中删除并不能简单地得出精神损害不可赔偿的结论。因此,即使《蒙特利尔公约》生效。关于承运人的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并没有完结,仍然将持续下去。
六、结 论
国际航空事故可能给旅客造成非常严重的精神痛苦,以致严重损害日常生活能力,这时有没有外部的身体伤害已经不重要了。法律的任务就是给予损害应得的救济。如果损害和事故有因果关系,毫无疑问,这种损害应该得到赔偿。目前,许多国家的国内法都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应该在《华沙公约》中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适当的位置。其次,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精神损害的本质不仅应从法律的角度也应该从医学的角度考虑。从法律的角度讲,法官先入为主地认为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有严格的区别,把法文本的“lesion corporelle”严格地解释为身体伤害更加剧了这种误解。从医学角度看,精神损害的根源是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会导致身体发生变化。精神损害本质上是一种身体损害,没有必要再为华沙公约是否涉及精神损害而争论不休。对国际航空旅行中可能产生的三种类型的精神损害尤其是纯粹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应该是国际航空法发展的趋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法学院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Singed at Warsaw on 12 October 1929(hereinafter Warsaw Convention),at http://www.jus. uio. no/lm/air.carriage. warsaw. convention. 1929/doc. html,art.17(emphasis added),last visited May 13,2003.
赵维田著:《国际航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Guatemala City Protocol 1971,at.http://www.fog.it/convenzioni/inglese/guatemala-1971.htm,art.17(emphasis added),last visited May 13,2003.
“Personal injury”的涵义是“非财产损害,而是对身体、心理或感情的伤害。比如如果你在杂货店踩到香蕉皮而跌倒,遭受的人身伤害包括实际的身体伤害和在公众面前跌倒时感到的羞辱,但是摔碎的手表不包括在内”(An injury not to property,but to your body,mind or emotions.For example,if you slip and fall on a banana peel in the grocery store,personal injury covers any actual physical harm(broken leg and bruises) you suffered in the as well as the humiliation of falling in Public,but not the harm shattering your watch),at http://www. nolo.com/lawcenter/dictionary/dictionary_listing. cfm/Term/DEEEOE11-E3A5-4E2D-9E36FA5CC1F46D61/alpha/P,last visited May 28,2003.
See Burnett v.Trans World Airlines,Inc.368 F.Supp.1152,(D. N. 1973),参见赵维田著:《国际航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See Rosman v.Tran。World Airlines,Inc.34 N.Y.2d 385(N.Y.A.1974).
See Husserl v. Swiss Air Transport Co,351 F.Supp.702(S.D.N.Y.1972),see also Ruwantissa I.R.Abeyratne,Mental Distress Aviation Claims-Emergent Trends,65 J. Air L. & Com. 227 (2000).
See Floyd v.Eastern Airlines,Inc, 872 F.2d 1462(11th Cir.1989).
See Eastern Airlines,Inc v Floyd,499 U. S. 530(1991),又见黄力华:《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从〈华沙公约〉到〈蒙特利尔公约〉》,载《民商法论丛》(第20卷),金桥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79-280页。
但有学者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分析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推理完全忽略了“lesion corpoprelle”该词在法语中的法律涵义。虽然lesion corporelle没有特别包括精神损害,但也没有特别证据表明该词特别排除精神损害。这一判决过分强调许多普通法系国家在1929年不承认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法院的这种分析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普通法系区分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法国民法没有相应的概念,不区分精神损害和身体损害,对于任何一种损害都给予赔偿,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借用普通法系的观点来分析以法文为正式文本的公约是不妥当的。其实法院的主要担心在于如果采用广义解释,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华沙公约》限制承运人责任、促进商业航空运输发展的目标就会受到打击。See J.Brent Alldredge,Continuing Questions in Aviation Liability Law: Should Article 17 of the Warsaw Convention Be Construed to Encompass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Emotional and Mental Distress,67 J.Air L.& Com.1360-1362(2002).
See 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56 F.Supp2d.1190(D.Mont.1999).
See Terrafrance v.Virgin Atlantic Airways,Ltd,151 F. 3d 108(3d Cir.1998). [page]
Alldredge,See J.Brent Alldredge,Continuing Questions in Aviation Liability Law:Should Article 17 of the Warsaw Convention Be Construed to Encompass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Emotional and Mental Distress,67J. Air L.& Com.,at 1366.
See Weaver v.Delta Airlines,Inc,211 F Supp.2d1252(D.Mont.2002).
See Alvarez v.American Airlines,Inc,No.98 Civ.1027,1999 WL 69129922,at*5(S.D.N. Y.Sept.7.1999).
In re Air crash Disaster Near Roselawn,Indiana on October 31,1994,法院认为Floyd案仅要求具体伤害是责任的前提要件,一旦这个前提条件满足,Floyd案并不明确禁止精神损害赔偿。此外,法院认为第17条仅明确要求损害和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没有暗示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才可以获得赔偿。虽该案中的精神损害不是由身体损害引起的,法院对遇难乘客遭受的恐惧仍给予了赔偿。
Larsen,Regime of Liabilit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Air Law-with Focus on the Warsaw system and the Montreal Convention of 28 May 1999,at http://www.rettid.dk/artikler/speciale-20020002.pdf,p33,last visited May 24,2003,at 38.
Article 24 of Warsaw Conventioin states: “In the case covered by Article 18 and 19 any action for damages,however founded,can only be brought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s set out in this conventiion. 2 in the case covered by Article 17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oceeding paragraph also apply,without perjudice to questions as to who are the persons who have the right to bring suit and what are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Warsaw Convention,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Singed at Warsaw on 12 October 1929 (hereinafter Warsaw Convention),at http://www.jus.uio.no/Im/air. carriage. warsaw. convention. 1929/doc. html,art. 17(emphasis added),last visited May 13,2003,art.24.
See Zicherman v·Korean Air Lines;516 U.S.217(1996),revg in part,43 F. 3d 18 (2d Cir. 1994).
See King(AP)(Respondent)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 (Appellants)(Scotland)In Re M(A Child by Her Litigation Friend CM)(FC)(Appellant),see also 8 Aviation,International Law Update 52-55(2002).
具体案情参见Morris v.KLM Dutch Airlines EWCA Civ 790(2001).
具体案情参见King 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 1 Lloyd's Rep 95(2001).
See King(AP)(Respondent) 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Appellants)(Scotland)In Re M(A Child by Her Litigation Friend CM)(FC)(Appellant).
《陆红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4期。
参见高万泉、丁小燕:《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载《法学》2002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2001年2月26日。
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2000-2001年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民事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 (hereinafter Montreal Convention),May 28,1999,ICAO Doc 9740.
参见唐明我:《新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责任制度及其影响》,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See Husserl v.Swiss Air Transport Co.,351 F.Supp.702(S.D.N.Y.1972),see also Ruwantissal. R.Abeyratne,Mental Distress Aviation Claims-Emergent Trends,65 J.Air L.&Com.227(2000),at 226.
See Husserl v.Swiss Air Transport Co.,351 F.Supp.702(S.D.N.Y.1972),see also Ruwantissal. R.Abeyratne,Mental Distress Aviation Claims—Emergent Trends,65 J.Air L.&Com.227(2000),at 257-258.
声明:该作品系作者结合法律法规,政府官网及互联网相关知识整合,如若内容错误请通过【投诉】功能联系删除。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