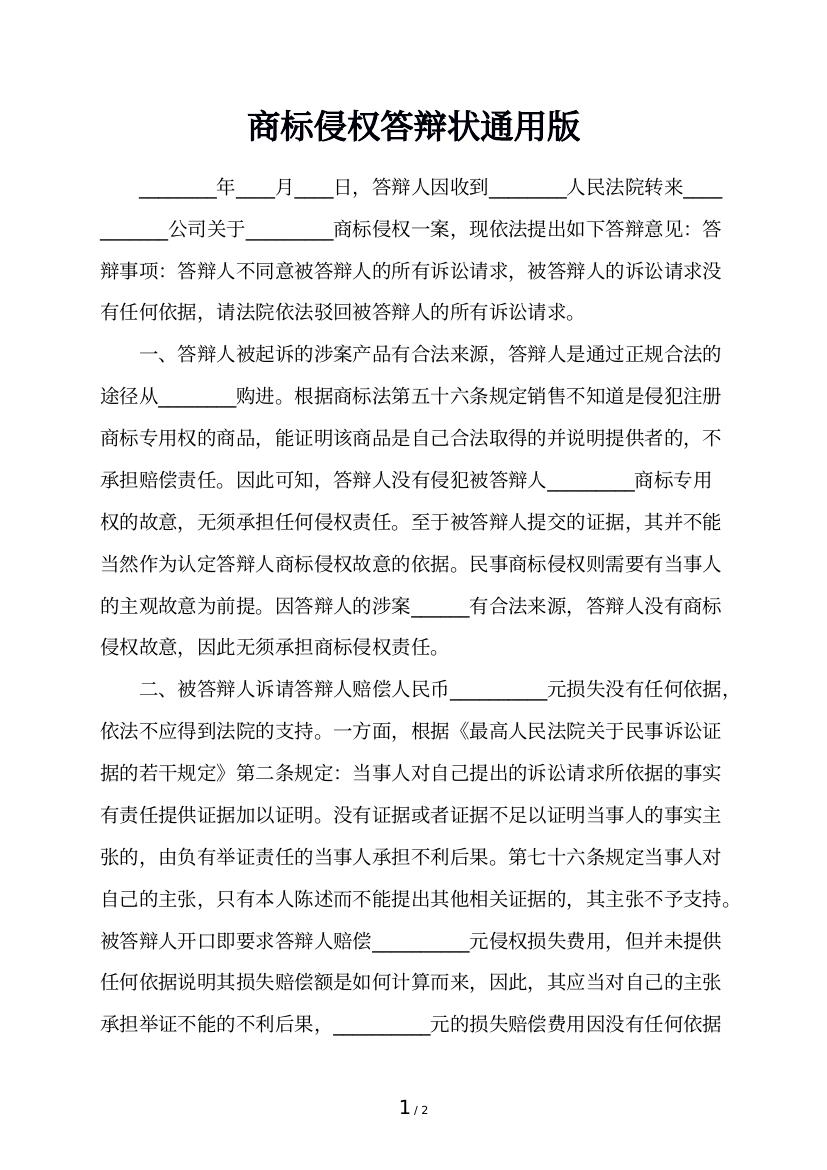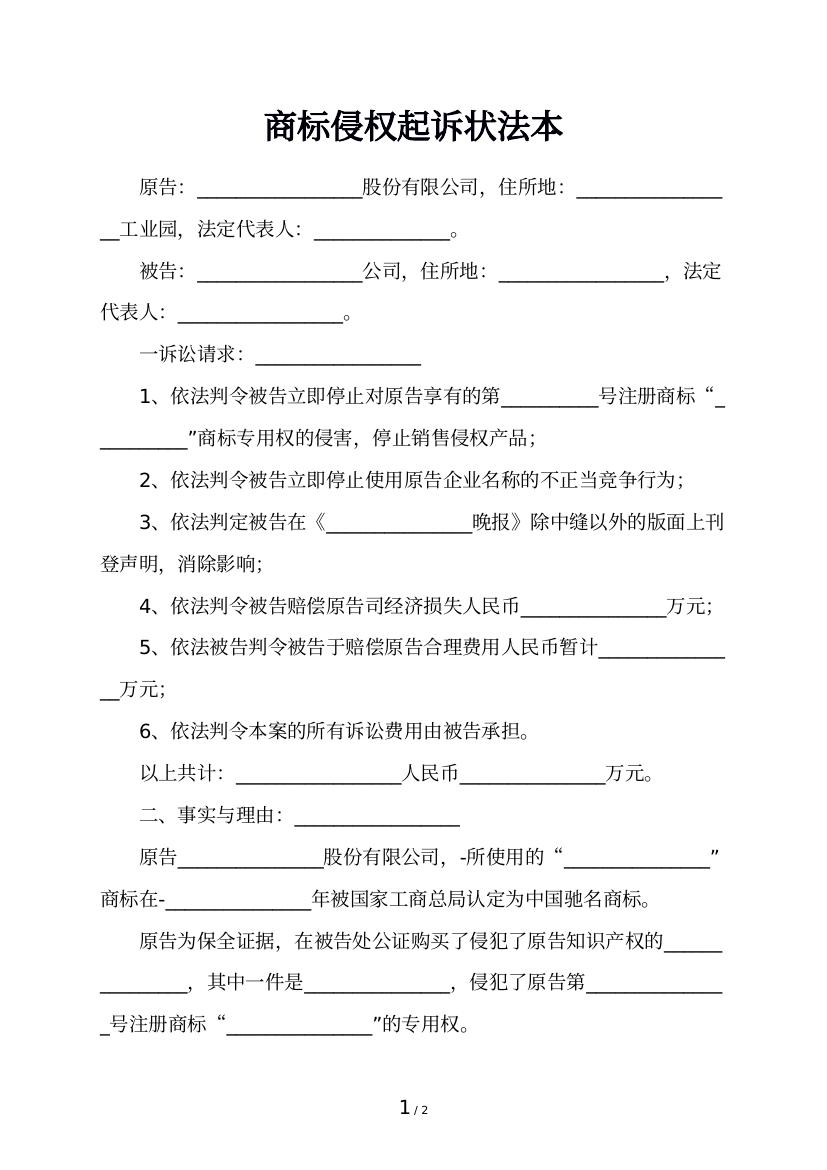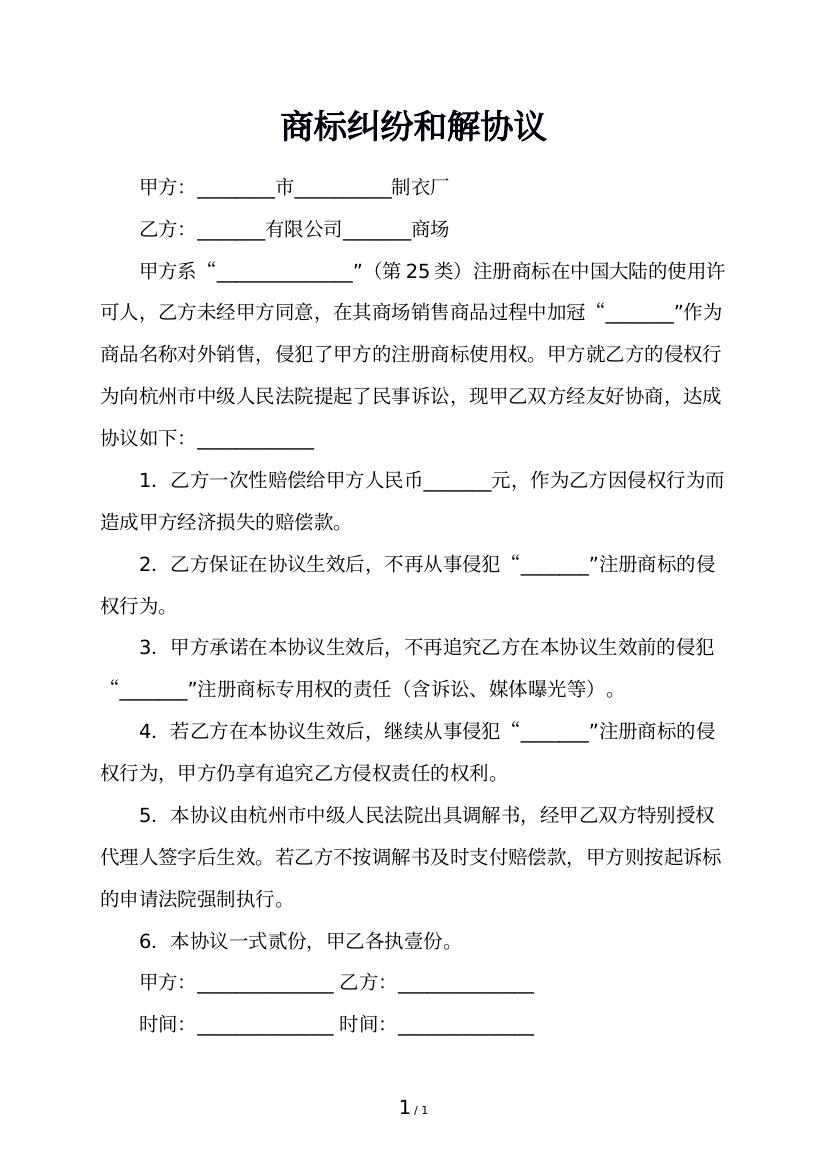商标间接侵权研究(二)
在Ciba-Geigy Corporation. v. Bolar Pharmaceutical Co, Inc.案中,原告Ciba公司于1970年获得了一种降压药的专利权。并在这种降压药上注册了名为Apresazide的商标。原告将降压药分别装在容量25毫克、蓝白色胶囊,以及容量50毫克、粉白色胶囊中销售。 [1] 原告的专利权于1981年届满后,被告Bolar公司开始生产与原告降压药类似的药物,并且在使用了上述两种规格、形状和颜色的胶囊,其外形与Apresazide牌降压药胶囊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两种胶囊之上分别印有两个公司的名称。 [2]
原告根据美国《商标法》和新泽西州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被告提出了两项指称,首先是被告在仿制药品上使用与其Apresazide牌降压药相同的胶囊,构成对商品来源的错误陈述,违反了禁止未经许可模仿“非功能性”商业外观的法律。其次是被告使用相同胶囊的目的就是促使药店或药剂师将被告的药品假冒为原告的Apresazide牌降压药出售;或者说被告对这一假冒后果至少能够进行合理的预期。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间接侵权”。 [3]
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原告在选择Apresazide牌降压药胶囊的颜色时完全时随意的,并没有任何医疗上的目的。其他制药公司也曾经制造出颜色不同的相同药品。同样,原告药品的大小和形状也没有医疗上的用途。这样,原告胶囊的颜色、大小和形状就只有识别药品来源的功能,即具有了“显著性”。 [4] 而证据表明,虽然被告的胶囊上印有自己公司的名称,但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多数已经超过60岁,其视力难以认清胶囊上的小字,以区分被告与原告在外观上相同的药品。因此被告使用与原告药品相同的商业外观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 [5] 同时,法院也根据证据认定:被告故意复制原告药品商业外观的主要动机是将促使药店和药剂师将其生产的药品以原告Apresazide牌降压药的价格出售。在原告可以合理预期药店和药剂师会用自己的药品假冒Apresazide牌降压药时,其继续供货的行为即已构成“间接侵权”,即使其没有其他引诱和鼓励假冒的行为。 [6]
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William R. Warner v. Eli Lilly案判决60年之后,在Ives Laboratories, Inc. v. Inwood Laboratories, Inc. 案中再一次陈述了商标“间接侵权”的规则。强调药品的商业外观如果具有“功能性”,就不能作为商标受到保护,仿制者如果故意引诱他人实施商标侵权,仍然要作为间接侵权者承担责任,但商标权人必须对此予以举证证明。
该案的基本事实背景和上述几个案例很相似:原告Ives公司制造享有专利的处方药抗栓丸,并注册了商标Cyclospasmo。在其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被告不但仿制这种药品,还使用了相同颜色的胶囊,同时在向药剂师寄送的产品目录中列出了自己仿制药品的价格与原告药品的价格,以示自己的药品便宜。而一些药剂师将被告的仿制药品装在自己的容器中、贴上原告的Cyclospasmo商标加以销售。原告依据美国《商标法》提起诉讼,首先认为被告故意使用与之相似的药品商业外观会会导致消费者对药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其次认为被告使用相似商业外观和发送价格比较广告的行为还意在诱使药剂师实施商标侵权行为,即构成“间接侵权”。 [7]
对于原告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关键在于原告药品的商业外观是否具有“功能性”,因为只有“非功能性”的商业外观才可能因具有“显著性”而作为非注册商标受到保护。被告对该商业外观的使用才可能构成“直接侵权”。对此,最高法院支持地区法院的认定,即原告药品的颜色对于患者和医生而言是“功能性”的,其原因在于许多老年患者是以药品的颜色来识别其治疗效果的。一些患者将不同的药物混放在一个容器中,并根据颜色区分不同的药物。 [8] 在这种情况下,药品颜色起到的作用并非区分来源于不同制药公司的同一类药品,而是区别不同种类的药品。换言之,对于抗栓丸而言,其蓝白相间的颜色是用于识别产品本身而非识别产品来源的,本身不具有“显著性”。这样,这种颜色就具有了“功能性”,不能作为未注册商标受到保护。因此,被告将药品制成与原告药品相同的颜色并不构成侵权。
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实施了“间接侵权”行为的指称,最高法院重申了60年前William R. Warner v. Eli Lilly案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即直接侵权者之外的人也可能承担商标侵权责任。最高法院指出:
“商标侵权责任可以扩展到实际错贴标签的人之外。即使生产者没有在销售链上直接控制他人,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要为他们的侵权活动承担责任。因此,如果制造者或销售者故意引诱他人侵犯商标权,或者如果其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他人正在实施商标侵权而继续向其提供产品,则生产者或销售者对这种欺骗所造成的损害要承担责任。” [9]
在本案中,那些将被告药品贴上原告商标出售的药剂师无疑直接侵犯了原告的商标权。而被告并没有实施同样的行为,而且由于原告药品的商业外观具有“功能性”,被告使用同样的外观也不构成“直接侵权”。这样,被告是否要为药剂师的商标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就取决于其是否故意引诱药剂师实施侵权行为,以及在知晓药剂师正在实施侵权之后,是否继续向其提供药品。
法院发现:被告的销售代表从未亲自拜访过药剂师,不可能以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语言引诱或促使药剂师将被告生产的药品贴上原告的商标出售。被告仅仅是向药剂师们寄送产品目录,并在其中将自己的药品与原告的同类药品进行了价格比较。 [10] 对此,法院认为:不能仅以被告进行价格比较的事实认定被告暗示药剂师们应当将自己的药品假冒为原告的药品出售。而且,虽然被告能够预见某些不道德的药剂师可能利用自己的药品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但被告毕竟无法准确地预见是哪些药剂师会这样做。因此也不能要求被告停止向所有药剂师提供与原告药品在外观上相似的药品。
Ives案对于澄清第二类商标“间接侵权”的构成有重大意义。它进一步说明了判断药品商业外观是否具有“功能性”的标准。通过对比上述Ciba-Geigy v. Bolar案和 SK&F. v. Premo案可以发现:药品的商业外观是否具有“功能性”并不能一概而论。当药品的颜色等外观成为患者识别一类药品的依据时,该外观就有“功能性”。反之,如果药品外观是患者区分不同制药公司生产的同类药品的手段,则该外观就不具有“功能性”,而是具有“显著性”,可以作为非注册商标受到保护。同时,Ives案也明确了判断商品提供者为下手经营者的商标侵权行为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标准:在没有使用他人商标或他人具有“显著性”的商业外观的情况下,仅仅一般性地预见下手经营者可能会将自己的产品假冒为他人的相似产品出售并不足以使商业提供者承担停止供货的责任。只有在其知晓或应当知晓某一特定下手经营者正在利用自己提供的商品从事商标侵权时,才应当采取包括停止供货在内的合理措施,否则构成“间接侵权”。这一规则避免了对本身没有实施假冒行为的商品提供者施加过重的侵权责任,有利于保障正常的经营秩序和维护利益平衡。[page]
(三)印刷商、广告商和包装商等制作、印刷商标标识或在包装上附着商标标识
如果印刷商、广告商和外包装生产商等专业服务提供者在知晓委托人没有获得商标权人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仍然接受委托而制作、印刷商标标识、在出版的广告宣传册或播出的广告节目中使用商标标识,或是在产品包装上附着商标标志,也会构成“间接侵权”。
这类以特定方式使用商标的行为与上述第一类“间接侵权”存在很大差异。除了下文所述的例外情况之外,上述第一类“间接侵权”明显具有利用他人商标牟取非法利益的意图。虽然将贴有他人商标的商品出售给“知假买假”的经销商并未导致混淆,但该商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清楚地知晓下手经营商会进行转卖,从而使消费者发生混淆。可以说,该制造商和销售商未经许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行为是最终侵权行为的源头,对消费者的混淆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且这类行为的实施者都是与商标权人具有竞争关系的相同或相似产品提供者,其行为所获得的利益直接来自于对他人商标中所含商誉的不当利用。因此,欧盟各国的商标立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才认为此种类型的侵权行为不仅是提供“侵权工具”的“间接侵权”,而是“直接侵权”。
与此相反,第三种类型行为是根据他人委托而实施的,委托者总会声称自己就是商标权人或被许可人,许多受托人也是相信委托人有权使用相关商标的,因此并没有直接利用他人商标牟取利益的意图。同时,受托人只是向委托人提供印制好的商标标识、贴上商标的产品包装或广告,除此之外并不向任何经营者或消费者提供。受托人的行为不但不会直接引起任何混淆,而且只要信赖委托人为商标权人,受托人也不会预期最终消费者会产生混淆。更为重要的是,受托人并非是商标权人的商业竞争者,他们就其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也并非利用他人商标中所含商誉的结果。即使委托人最终利用受托人提供的服务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受托人的服务也只起到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因此,此类行为不应被界定为“直接侵权”,而只能在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构成“间接侵权”。美国《商标法》和英国《商标法》均将这类行为规定为或解释为“间接侵权”。美国《商标法》规定:对于未经许可而复制、伪造、抄袭或仿冒他人注册商标标志并将其附着在标签、标记、印刷品、包装、容器或广告中,意图在商业活动中用于对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推销、分发或广告宣传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知晓该仿冒的商标意图被用于导致混淆、误认或欺骗,商标权人就可以获得损害赔偿并追索利润。 [11] 为了明确起见,美国于1998年修订后的《商标法》还特定规定:如果“仅从事印刷标志业务的侵权者或违法者”或“仅从事在报纸、杂志或其他类似媒体及电子媒体中从事广告业务的侵权者或违法者”为“无辜侵权者或无辜违法者”(innocent infringer or innocent violator),商标权人仅能获得禁止其在今后从事类似印刷他人商标或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商标的禁止救济。 [12]
英国1994年《商标法》规定:将注册商标附着于物质材料之上,并意图将其用于商品的标签或包装,或用于商业文件,或用于对商品或服务的广告者,如果知道或有合理的理由知道这种行为没有获得商标权人或其被许可人的授权,对于他人使用该物质材料侵犯注册商标权的行为,应被视为侵权者。 [13]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商标法》是在以与欧共体《一号指令》和《欧共体商标条例》基本相同的用语界定了“直接侵权”行为和“对商标的使用”之后,对上述行为加以规定的。 [14] 这说明即使是在将商标“直接侵权”作较广范围界定的欧盟国家,也并不认为此类受托行为是“直接侵权”。 [15]
美国和英国的法院在实践中也确认了这种行为只能构成“间接侵权”。美国法院在判例中曾指出:只要广告商无意出售贴有他人商标的商品,广告商就不能构成“直接侵权”,只能被控“间接侵权”。 [16] 英国法院也认为:同样是将商标附着于产品外包装的行为,如果在附着商标时商品本身已经被包装好了,该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即将上述第一种提供“侵权工具”的行为认定为“直接侵权”),但如果当时外包装中还没有商品,在包装上贴商标的人仅是提供外包装本身的,则只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构成“间接侵权”。 [17]
判断受托人是否构成此种类型“间接侵权”的关键仍然在于如何从外部事实认定受托人的“知晓”。美国法院长期以来的判例认为:受托人对于委托人是否有权使用相关商标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如果受托人在提供印刷、广告等服务时,明知委托人意图借助委托服务实施侵权,或者作为一个“理性人”本来应当知道,却因不负责任、对委托事务的合法性漠不关心(reckless disregard)而未能发现事实真相,就具有主观过错、构成“间接侵权”。 [18] 而被使用商标的知名程度、委托人提供的证明的可信度、受托人以往接受合法委托的经历等都可以作为推断受托人主观意图的因素。在Polo Fashions v. Ontario Printers案中,法院指出:
“商人们不能那么单纯,像驼鸟一样将脑袋埋入沙子里而忽视对一个理性的商人而言轻易就能发现的明显事实。是否存在侵权意图应当根据客观的、理性商人的标准,而不是根据主观的心理状态进行判断……当某人要求制造商或印刷商为某著名厂商制造产品时,受托人有判断委托人合法性的积极义务,受托人必须进行合理调查……一个商人不能仅仅接受订单而不去(对订单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否则他将承担被判定为商标侵权承担责任的风险。” [19]
(四)有意向售假者提供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提供者向分散的经营者出租摊位是常见的商业运作模式,但租用摊位的小经营者却常有出售假冒商品的情况。对此,商标“间接侵权”的基本规则仍然适用:如果场所提供者知晓其中的经营者有出售假冒商品等侵权行为,但却置若罔闻,不采取合理措施加以制止,而仍然向其提供场所和辅助服务,无异于在纵容和帮助经营者实施商标侵权行为,应当作为“间接侵权者”承担法律责任。在美国,曾有场所提供者提出美国《商标法》只规定那些“使用、复制、伪造、抄袭或仿冒”他人商标的侵权者应承担责任,并没有规定场所提供者也要承担责任。而美国法院则驳斥了这一说法,认为美国法院长期以来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商标“间接侵权”规则完全可以适用于场所提供者。 [20] 美国纽约州的《房地产法》还直接规定:房产业主如明知他人准备将房产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于非法制造产品或进行非法交易,而仍然租借或允许他人占有房产,则业主应当对由该非法活动造成的损害与房客或占有人负连带责任。 [21] 该《房地产法》甚至赋予了房产业主立即驱逐房客的权力:当房客或其他占有人利用房产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于非法制造产品或进行非法交易时,出租房产或允许他人使用房产的合同即失去约束力,房东可以立即收回房产,或据此提起要求收回房产之诉。 [22][page]
在1996年美国发生的Fonovisa v. Cheery Auction案中,一家二手货市场中有一些摊位大量出售盗版和假冒他人商标的唱片,警察和权利人曾经向场所提供者发出警告函、告之其市场中发生的侵权行为,而场所提供者却未能采取措施。法院发现场所提供者在明知部分摊位从事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还通过提供摊位、设施、停车位、广告、水管维修和顾客等方式对其进行实质性帮助。法院因此认定:“一个无视其中贩卖者肆无忌惮的商标侵权行为的二手市场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并判决该二手市场的管理者构成“间接侵权”。 [23]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法院认定场所提供者构成“间接侵权”的标准较商标印刷者等严格。其原因可能在于商标印刷者在接受委托时,有充分的机会对委托人是否为商标权人或被许可人逐一进行调查,因此如果印刷者故意不对委托事务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就可推定其具有过错。而在某一场所中却可能同时存在众多租用摊位的经营者,场所提供者并不可能一一了解、查实各经营者的行为。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有经营者出售假冒商品就认定场所提供者明知这种侵权行为而予以纵容,否则将会使场所提供者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影响正常商业活动的开展。
在著名的Hard Rock Café v. Concession Services案中,被告之一CSI公司经营着商品交易市场,并将摊位加以出租、收取摊位租金、保证金和商品存储费。被告在市场中张贴了禁止出售“违法商品”的告示,还聘了两个退休警察,在维持秩序的同时查看商户们是否遵守了自己的要求。被告的经理一天会在市场中来回巡视5次。如果商户有出售违法商品的行为,被告有权将其清退出市场。原告Hard Rock咖啡公司在T恤衫上享有“Hard Rock”商标,在发现被告的市场中有商户出售假冒的“Hard Rock”牌T恤衫之后,原告起诉了被告。 [24] 由于被告没有直接实施商标侵权行为,因此其行为只可能构成“间接侵权”。而是否侵权则首先取决于被告是否知晓或有理由知晓其市场中的商户正在进行商标侵权。
地区法院以两点理由判决被告知晓其商户的侵权行为:(1)被告“故意对在其市场有假货出售的行为视而不见”;(2)被告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在其市场发现或阻止出售假货的行为。 [25] 在上诉审中,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并不同意第二点理由。上诉法院指出:“间接侵权中‘有理由知晓’的标准要求象一个理性人那样行事,但并没有施加任何寻找并阻止侵权行为的义务。” [26] 这就意味着场所提供者即使事先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阻止商户出售假冒商品,也不能仅就此推定其实际知晓或应当知晓商户出售假冒商品的事实。虽然上诉法院认同“对侵权行为视而不见(willful blindness)”就等于“实际知晓”的结论,但强调它的构成要件是“在强烈怀疑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故意不进行调查”。 [27] 由于地区法院的判决将注意力集中在被告没有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而没有讨论被告是否应当像理性人那样应当发现侵权事实,或者故意对侵权事实视而不见,上诉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
五、我国《商标法》应合理地划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款对商标“间接侵权”是有原则性规定的:“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虽然该条款并未明确说明这种行为属于“间接侵权”,但由于其以“故意”和帮助他人实施商标侵权为构成要件,此种行为是对商标权的间接侵犯应属无疑。在2005年发生的“路易威登诉北京市秀水豪森服装市场有限公司等案”及2006年发生“路易威登诉北京朝外门购物商场案”中,法院正是以这一条款为依据认定秀水市场管理者及北京朝外门购物商场在明知其经营场所中有商户出售侵权商品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属于为商户的侵权行为故意提供便利条件的侵权。 [28] 但是,这一条原则性规定还远不足以构建完善的商标权“间接侵权”制度。
《商标法》第52条列举了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5种行为,分别是:(1)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2)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4)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5)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由于第52条在列举这5种行为时,却均未以“主观过错”作为侵权构成要件,根据知识产权侵权原理,只能将这5种行为理解为“直接侵权”。这意味着行为人只要在客观上实施了这些行为,均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直接侵犯。然而,从立法技术角度看,第52条的规定存严重缺陷:它没有对“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这两种构成要件截然不同的商标侵权行为进行正确区分,而是混为一谈,并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严重问题。
(一)《商标法》的缺陷之一:没有将“导致混淆”作为构成“直接侵权”的条件
绝大多数国家的商标立法都规定:在同种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和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都必须以“导致混淆”作为构成直接侵犯商标权的条件。如前文引述的美国及欧盟的商标立法。而有些国家之所以没有将“导致混淆”作为“在同种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构成商标直接侵权的前提,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这一默认的结论是无需商标权人再加以证明的。如前文所述,由于传统商标法的基本功能就是防止消费者对商品来源发生混淆,因此“混淆”应当是构成商标“直接侵权”的基本条件。如果提供使用了注册商标的商品本身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则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而《商标法》在规定5种“直接侵权”行为时却根本没有提及“混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以消费者的“误认”或“混淆”作为判决商标是否“近似”,以及商品是否“类似”的依据, [29] 但这与在使用商标而“导致混淆”仍然是有区别的。因为即使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以及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了近似商标,甚至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了相同商标,也完全可能因为特定原因而不可能导致混淆。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使用商标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是缺乏法理依据和不公正的。[page]
2000年发生的“美国耐克公司诉银兴制衣厂案”充分反映了我国《商标法》中的这一缺陷。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在注册了“耐克”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是运动服装、而西班牙Cidesport公司则在西班牙的同类商品上合法拥有“耐克”商标。西班牙Cidesport公司委托浙江省嘉兴市银兴制衣加工厂制作滑雪夹克,并缝制“耐克”商标标识。成品由浙江省畜产进出口公司负责出口至西班牙。美国耐克公司发现上述行为后,申请海关扣押了这批滑雪夹克并起诉了西班牙Cidesport公司、银兴制衣加工厂和浙江省畜产进出口公司。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西班牙Cidesport公司与两中国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这批带有“耐克”商标的滑雪夹克全部出口至西班牙加以销售,并不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虽然美国“耐克”标志与西班牙“耐克”相同,也被使用在相同的商品上。但两中国公司的制造和出口行为不可能引起中国相关公众的混淆,也不会给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的商标权造成任何损害。但是,由于我国《商标法》只是简单地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构成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而没有将“导致混淆”作为构成要件,审理此案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即以中国公司在同类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为由,判决两中国公司败诉。 [30]
根据上述美国《商标法》的规定,这种不可能导致混淆、误认或欺骗的商标使用行为根本就不能构成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而依据Gilson的“侵权工具”理论,只向下手经营者提供商品,而不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制造商或经销商并不会构成“直接侵权”。只有其在知晓下手经营者会将商品以导致消费者混淆的方式提供时,才构成“间接侵权”。我国法院将中国企业接受“定牌生产”委托、使用外国商标权人商标并仅销售到委托人所在国家的行为认定为对中国商标权人的“直接侵权”,不但违反商标法的基本原理和立法目的,而且会导致我国对商标权的保护水平超过发达国家,对于广大出口加工企业的利益会造成不公正的严重损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4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已经认识到了《商标法》中的这一缺陷。针对“受境外商标权人委托定牌加工的商品仅用于出口,其商标与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北京市高院指出:“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定牌加工是基于有权使用商标的人的明确委托,并且受委托定牌加工的商品不在中国境内销售,不可能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应当认定构成侵权”。但是,在《商标法》没有将“导致混淆”作为认定构成“直接侵权”前提的情况下,这一正确观点很难被其他地方的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所接受。2006年2月,常州某厂商因接受尼日利亚有关定牌加工“Mack”牌汽车配件的订单,而受到“Mack”商标在中国的商标权人(美国公司)所举报,最终被常州工商部门认定侵权。 [31] 这说明在《商标法》中明确“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不同构成要件已经刻不容缓。
(二)《商标法》的缺陷之二:错误地将擅自制造商标标识界定为“直接侵权”
第52条的第二个重大缺陷在于错误地将擅自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定为“直接侵权”而非“间接侵权”。其第3款规定:“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属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同样,由于没有将“导致混淆”作为构成这种“直接侵权”的前提,第52条第3款可导致一个在逻辑上和实践中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即只要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加以销售的,即使该商标标识并未被用于相同或同类商品,没有导致消费者的混淆,也构成“直接侵权”。这样,如果在上述“耐克案”中,西班牙公司仅仅委托中国公司制造“耐克”商标标识并将之运回西班牙,中国公司的“制造和销售”商标标识的行为仍然会构成对美国公司商标权的直接侵犯。
这一结论不但与美国《商标法》的规定大相径庭,而且也与英国等欧盟国家的商标法相冲突。这使得我国对于商标权在这方面的保护水平实际上大大超越了发达国家。如上文所述,美国《商标法》并不将制造商标标识行为本身定为“直接侵权”,而是规定只有印刷商在知晓委托人没有获得商标权人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制造商标标识的,才可能构成“间接侵权”,英国《商标法》对此有相同的规定。
在英国发生的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Ltd v. Mitchel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案与上述我国的“耐克案”如出一辙。Beautimatic公司在英国是Lexus商标的权利人。Mitchell公司在国外市场上销售贴有Lexus商标的同类商品,并委托位于英国的Nuline公司制造Lexus商标标识和贴有该标识的外包装,以及生产贴有该商标的产品,并全部用于出口。Beautimatic公司起诉Mitchell公司和Nuline公司侵犯其商标权。英国高等法院指出:要构成商标侵权(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侵权),相关商标必须被用于相同或同类商品,而且使用必须发生英国境内。而制造商标标识,并将商标标识或贴有该标识的包装运到国外、用于相同商品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在英国境内用于相同商品。 [32] 英国法院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混淆问题,但由于商标和带有商标的包装不在英国境被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就不可能导致英国的相关公众混淆,因此英国法院认定被告不构成商标侵权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仍然是这种对商标的使用不会导致混淆。虽然英国法院同时认定在英国境内只要将商标用于商品之上,即使商品全部用于出口也构成对商标权的直接侵犯。但这是由于法院将“导致混淆”进行了过大的解释,即认为“负责包装的人、将商品运输出国的人、负责商品检验的人,以及碰巧偶然看到商品的人”都会因为看到商品上的Lexus商标而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 [33] 这实际上是将“混淆”的范围从准备按照商标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和其他相关公众扩大到了一切在出口环节中可能偶然接触到商品的人,显然是一种对商标权的过高保护,并不应当为我国所效仿。[page]
(三)应合理地划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确立商标“间接侵权”制度,不仅是为了适当扩大以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更好地维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通过正确地划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间的界限,而对构成“直接侵权”的行为范围加以适当限定,防止对商标权过高水平的保护。具体而言,在修改《商标法》时,对有关商标侵权行为的条款应当重新加以设计。在立法模式上,欧盟模式——只将“导致混淆”作为“在同类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和“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这三种行为构成“直接侵权”的前提,同时直接规定“在同类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构成“直接侵权”,并不值得我国效仿。其原因在于即使是未经许可“在同类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在某些情况下也未必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这一点在我国企业接受外国商标权人定牌加工委托的交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对“导致混淆”不进行限制性解释的情况下采用欧盟模式将会使许多中国企业因定牌加工行为而被判定构成商标侵权。这将导致我国对商标权的过度保护,从而损害国内企业的利益。
相比之下,美国模式——将“导致混淆”明确规定为构成“直接侵权”的必要条件应当为我国所效仿。这种立法例不但符合商标法防止混淆的基本立法目的,也可以避免将接受国外商标权人委托进行定牌加工的行为认定为“直接侵权”。同时还可以纠正现行《商标法》第52条第3款将擅自制造他人商标标识界定为“直接侵权”的错误。而在对“导致混淆”的解释中, Gilson的“侵权工具理论”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该理论的关键是只将直接导致混淆的行为界定为“直接侵权”,而把其他提供贴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定为“提供侵权工具”,在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构成“间接侵权”。如上文所述,“侵权工具理论”表面上的缺陷在于:提供贴有他人商标的商品是否构成“直接侵权”要取决于提供者的直接下手是否发生混淆,导致同一种行为会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法律性质。但是,从实践角度来看,商标权人关心的并不是侵权人构成的是“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而是能否获得赔偿。“侵权工具理论”则同样能够使商标权人获得充分的救济:如果向一名知晓商品真实来源的下手经营者出售贴有他人商标的商品,只要提供者知晓或有理由预期下手经营者会向公众出售该商品、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就属于在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向他人提供“侵权工具”,其行为仍然构成“间接侵权”,并应与直接侵权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在采纳“侵权工具理论”时,只要合理地设计认定商品提供者“主观过错”的规则,就能够既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又避免对商标权的过度保护。
对我国商标立法而言,可以在效仿美国模式,将“导致混淆”作为所有“直接侵权”前提的情况下,进一步规定:如果在同类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并向他人提供,只有在能够证明接受商品者不会发生混淆,以及不知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知晓接受者会以导致他人混淆的方式使用该商品时,才不承担侵权责任。而在同类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和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则只有在导致接受商品者发生混淆,或者知晓以及有合理的理由知晓接受者会以导致他人混淆的方式使用该商品时,才承担侵权责任。由于在同类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一般均会导致接受商品者的混淆,如向下手经营者提供该商品,一般也能合理预期到下手经营者会向消费者提供、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因此在被控侵权者无法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即可以认定该行为构成“直接侵权”。但在被控侵权者能够举证证明不会直接导致混淆,也无法预期接受商品者会以导致混淆的方式使用商品时,则不应认定侵权行为成立。通过这种对举证责任的设计,能够在不加重商标权人举证负担的情况下,适当限制“直接侵权”范围。如果按此标准处理“耐克案”,接受西班牙公司委托进行定牌加工的中国厂商就可以通过证明这批“耐克”运动鞋只向西班牙商标权人提供、不可能在中国相关公众中导致混淆而免于被认定为构成侵权。
六、我国《商标法》应合理地规定各种“间接侵权”的情形和构成要件
在正确划定“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界限的基础之上,我国《商标法》还应当分别规定各种构成“间接侵权”的情形和构成要件。如上文所述,“间接侵权”不但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同时对于不同的行为,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的标准也应有一定差异。如美国法院认为商标标识印刷者有义务调查委托人是否具有合法授权,但却判定场所提供者没有事先采取措施防止租用摊位者进行商标侵权的义务。对不同类型的行为人施加不同的“注意义务”反映了在保护商标权方面利益平衡的考虑。我国商标立法中有关“间接侵权”的规定只有《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第2款,不仅远不足以涵盖常见的“间接侵权”类型,也没有详细地列举各种“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如此原则性的规定会导致法官们对同样的案情出现不同的观点和判决结果,从而影响法律在适用上的稳定性。
2005年发生的“路易威登诉北京朝外门购物商场案”(以下简称“朝外门购物商场案”)就是这一立法不足的典型反映。该案的被告是经营场所的提供者——朝外门购物商场。原告为世界知名品牌“路易威登”在中国的商标权人,在发现被告商场地下一层中有商户出售假冒商品之后,即向被告发出函件,要求其制止侵权行为。朝外门购物商场在接到函件后,对出售侵权商品的商户采取了一定措施。如与其签订了《禁止销售未经授权著名品牌商品的责任书》、对3家商户进行处罚并清退了其中一家。但原告随后又能在原商户和其他众多商户处买到侵权商品,原告因此指称被告为侵犯他人商标权的行为提供便利,应承担侵权责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既然与商户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就有权利和义务“对市场进行管理及以对商户出售商品的种类、质量等进行监督,特别是应制止、杜绝制假售假现象。”而原告两次在其市场买到侵权商品的事实则“说明被告没有尽到其应负的经营管理责任及监督责任,主观上存有过错”。特别是原告在向被告致函交涉之后,第二次仍然可以在被告市场众多商户处购买到侵权商品,“表明被告未尽经营管理、监督责任的主观过错程度比较严重”。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为侵权商户的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应承担侵权责任。[page]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理由存在重大缺陷。法院的主要逻辑是:(1)场所提供者“有义务对商户出售商品的行为进行监督,制止、杜绝制假售假现象”。(2)商标权人两次在被告市场中买到了侵权商品,“说明被告(场所提供者)没有尽到其应负的经营管理责任及监督责任,主观上存在过错”。 [34] 这实际上是以场所提供者有查找、预防商户侵权行为的义务为前提,以场所中存在商标侵权行为的事实推定场所提供者具有主观过错。
这一逻辑在法院判决中的理由顺序安排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没有提及原告警告函的情况下,仅仅以场所提供者具有监督商户行为、制止侵权行为的义务和有商户出售侵权商品为由说明场所提供者“有主观过错”。然后才提及商标权人在致函后仍能在众多商户买到侵权商品的事实说明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比较严重”。换言之,在法院看来,场所提供者的“主观过错”本身来源于其在有监督义务的情况下市场中出现了侵权商品,而并非来源于收到商标权人致函后没有及时对售假商户采取措施。这一认定场所提供者“主观过错”和“间接侵权”的规则远较上述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Hard Rock Café案中确立的规则严格。它甚至意味着只要商标权人在市场中发现了侵权商品,即使不发出警告函告之场所提供者,也无法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场所提供者知晓或应当知晓有商户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场所提供者也会被认定为构成“间接侵权”。因为按照法院的观点,任何场所提供者都“有义务对商户出售商品的行为进行监督,制止、杜绝制假售假现象”,而商标权人能够在该场所购买到侵权商品的事实就能“说明”场所提供者没有尽到其应负的经营管理责任及监督责任以及主观过错。
更为严重的是,从法院的判决来看,场所提供者在接到商标权人致函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与商户签订《禁止销售未经授权著名品牌商品的责任书》、处罚对3家商户进行处罚并清退其中一家,都不足以推翻法院对其主观过错的推定。这实际上是对场所提供者施加“严格责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大量经营者,特别是个体经营者的知识产权意识尚有待提高,许多人也乐于以低价购买假货,以致于许多类似于朝外门购物商场的经营场所都有假冒商品出售的情况下,对场所提供者施加如此之高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实际上将使大量场所提供者轻易成为“间接侵权者”。这不但会阻碍商品交易市场的建立和运作,也会使我国在这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超越发达国家,显然是不足取的。
实际上,本案法院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商标“间接侵权”的原理,并综合本案的事实和现实情况,是有可能以合理的依据得出被告构成“间接侵权”的。正如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Hard Rock Café案中指出的那样:场所提供者本身并没有采取合理措施在其市场发现或阻止售假行为的义务,但如果其没有尽到一个理性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发现市场中的侵权行为,或者“在强烈怀疑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故意不进行调查”,即“故意对在其市场有假货出售的行为视而不见”,则构成“间接侵权”。换言之,法院应当做的不是从市场中存在侵权商品的客观事实推定场所提供者的主观过错,而是从双方举证中发现并论述场所提供者在知晓或应当知晓其商户出售侵权商品而不予制止或未采取相应措施的事实。
例如,在本案中,商标权人第一次在某一特定商户买到侵权商品之后,即向场所提供者致函交涉。而相隔一个月后,商标权人又在同一商户买到了相同的侵权商品,而在此期间场所提供者没有对该商户采取任何措施。这足以说明场所提供者在已经知晓该商户实施商标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对其商户的侵权行为加以纵容。 [35] 法院就可认定其行为因具有主观过错而构成“间接侵权”。即使场所提供者后来对该商户采取了措施,但仍然应当对在收到商标权人致函后一段合理时间至采取措施之间该商户实施的商标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值得注意是:在“路易威登诉北京市秀水豪森服装市场有限公司等案”(以下简称“秀水街案”)中,同样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基于与“朝外门购物商场案”相似的事实,却以相对合理的理由做出了认定场所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判决。在该案中,原告“路易威登”的商标权人在被告管理的秀水街商厦内,从某摊位上买到了侵犯其商标权的商品。原告随即致函被告,告之其市场内存在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并列出了销售者的摊位号,包括其买到侵权商品的摊位。而在半个月之后,原告又在相同的摊位第二次买到了侵权商品,并将被告诉诸法院。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场所提供者在收到原告的致函之后,没有对出售侵权商品的摊位经营者采取任何防治措施制止其侵权行为的继续,使得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故可以认定被告为其商户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36] 在上诉审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在收到原告的函件后,即应当知道其市场内有侵犯原告商标权的情形,但却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导致特定侵权商户仍能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属于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为其特定商户的侵权行为提供便利。 [37] 二审法院据此维持了原判。
“秀水街案”与“朝外门购物商场案”虽然在判决结果上相同,但在判决理由上却有极大区别。在“朝外门购物商场案”中,法官认定被告具有主观过错,即知晓其场所中有侵权商品出售的原因是并不是被告在收到原告函件后没有采取措施,而是认为被告具有监督商户行为、杜绝侵权行为的义务,以及市场中出现了侵权商品。而审理“秀水街案”的法官则是以被告在收到原告函件作为认定被告知晓其市场中有特定商户出售侵权商品的依据。虽然该案判决书也提及了被告“负有维护市场秩序、制止违法行为,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等的合同义务”,但只是将其作为被告知晓侵权行为之后应当采取措施的理由,而没有作为推定被告知晓其市场中有侵权行为的依据。两相比较,“秀水街案”判决中法官认定场所提供者主观过错的规则远较“朝外门购物商场案”宽松与合理。它意味着不能仅从市场中出现了出售侵权商品的现象,就推定场所提供者在知晓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有意为侵权者提供便利条件,而是要求有一定证据证明场所提供者确实知晓或至少应当知晓侵权行为的存在。这不仅符合国际上认定场所提供者构成商标“间接侵权”的标准,也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page]
无论怎样,同一个法院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对两起相似案件竟然适用了两种相去甚远的“间接侵权”认定标准,不但说明对商标“间接侵权”的研究尚不深入,更反映出立法上相应规则的缺失。因此,在下次修订《商标法》时明确列举各种商标“间接侵权”的情形,并列举其构成要件,应当是商标立法应当采取的对策。 注释:
[1] See Ciba-Geigy Corporation. v. Bolar Pharmaceutical Co, Inc., (3rd Cir )747 F.2d 844, at 848 (1984)
[2]同上, at 849
[3]同上
[4]同上, at 850
[5]同上, at 851
[6]同上, at 852-853
[7] Inwood Laboratories, Inc.,v. Ives Laboratories, Inc. 456 U.S 844, at 849 (1984)
[8]同上, at 853
[9]同上, at 853-854
[10]同上,at 852
[11] See 15 USC 1114(1)(b)
[12] See 15 USC 1114 (2)(A)(B)。“无辜侵权者”的用语很容易使用使人认为这类印刷者和广告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直接侵权”,因为根据美国《版权法》,未经许可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受5大“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仍然构成“直接侵权”,侵权人也被称为“无辜侵权者”。但如上文所述,商标权与版权毕竟有所不同,而且《不正当竞争法重述》、美国学者和法院均将印刷者和广告提供者的这种侵权行为称为“帮助侵权”而非“直接侵权”,Se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26 (1995), Jerome Gilson, Trademark Protection and Practice § 11.02 (i)(C)(III),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06); Century 21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of Northern Illinois v. R.M. POST, Inc, 8 U.S.P.Q.2d 1614, at 4 (1998)
[13] See Trade Marks Act 1994, Sec 10(5)
[14]英国《商标法》第10条(1)、(2)款和第(4)款根据《一号指令》和《欧共体商标条例》分别规定了对普通商标的“直接侵权”行为和“使用商标的行为”,而第(5)款则是对“间接侵权”行为的规定。见Trade Marks Act 1994, Sec 10(1)(2)(4)(5)。英国学者也将第(5)款解释为“间接侵权”,See William Cornish, David Llewely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Copyright, Trade Mars and Allied Rights (5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03) p.700
[15]英国学者指出:该条将侵权责任拓展到将他人注册商标附着于物质材料之上的标签、包装瓶生产商和印刷商,只要他们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该附着行为是没有经过授权的,See Duncan Mckenzie Kerly, Kerly on Trademarks and Tradenames from Sweet and Maxwell, Sweet & Maxwell, Ltd (2005) 14-036
[16] See Century 21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of Northern Illinois v. R.M. POST, Inc, 8 U.S.P.Q.2d 1614, at 4 (1998)
[17] See Beautimatic v Mitchell [2000] F.S.R. 267, Duncan Mckenzie Kerly, Kerly on Trademarks and Tradenames from Sweet and Maxwell, Sweet & Maxwell, Ltd (2005) 14-036
[18] See World Wrestling Federation, Inc. v. Posters, Inc.58 U.S.P.Q.2D 1783, 1784(N.D.Ill.2000)
[19] See Polo Fashions, Inc. v. Ontario Printers Inc, 601 F.Supp. 402, at 403-404 (N.D. Ohio 1984)
[20] See Polo Ralph Lauren Corporation v. Chinatown Gift Shop. 855 F. Supp. 648 at 650 (S.D.N.Y. 1994)
[21] See New York Real Property Law, 231(2)
[22] See New York Real Property Law, 231(1), 715(1)
[23] See Fonovisa, Inc. v. Cherry Auction, Inc., 76 F.3d 259, at 264-265 (9th Cir. 1996)
[24] See Hard Rock Cafe Licensing Corporation. v. Parvez, 1990 U.S. Dist. LEXIS 12146, at 1-6 (N.D. Ill., 1990)
[25] See Hard Rock Cafe Licensing Corporation. v. Parvez, 1990 U.S. Dist. LEXIS 12146, at 1-6 (N.D. Ill., 1990)
[26] See Hard Rock Café Licensing Corporation v. Concession Services, 955 F.2d 1143, at 1148-1149 (7th Cir. 1992)
[27] See Hard Rock Café Licensing Corporation v. Concession Services, 955 F.2d 1143, at 1149 (7th Cir. 1992)
[28]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二中民初字第2140号,及 (2005)二中民初字第13594号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1条
[30]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深中法知产初字第55号
[31]参见陆燕、许润润:《外贸定单标注商标须谨慎》,《中国知识产权报》2006年4月21日第7版
[32] See 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Ltd v. Mitchel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 Ltd and Alexir Packaging Limited, [1999] E.T.M.R. 912, 919
[33] See 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Ltd v. Mitchel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 Ltd and Alexir Packaging Limited, [1999] E.T.M.R. 923
[34]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二中民初字第2140号
[35]此案的判决书记载,原告于2005年9月20日在1D-063和1D-075商户处买到了假冒的LV包,并于9月29日就此向被告致函,而原告在同年10月27日又在1D-063和1D-075商户处买到了假冒的LV包
[36]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二中民初字第13594号
[37]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高民终字第335号